納粹大屠殺
针对犹太人的屠杀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納粹大屠殺(德語:Holocaust;希伯來語:הַשׁוֹאָה,羅馬化:HaSho』ah;意第緒語:חורב',Hurban)又稱猶太人大屠殺,指的是納粹德國及其協作國對近600萬猶太人進行的種族滅絕行動[2]。當時全世界有1500萬猶太人,而歐洲總共有近900萬猶太人,其中近三分之二被害[3],包括近150萬兒童[4]。一些學者稱大屠殺亦當涵蓋近500萬非猶太遇難者,由此總受害人數將達到近1,100萬人。屠殺發生於納粹德國、德佔歐洲地區及德國盟國所控區域[5]。
1941年至1945年,納粹對歐洲諸種族及政治群體展開迫害,猶太人遭到廣泛系統性屠殺,其規模為史上最大[6]。在納粹黨領導及黨衛隊協調之下,德國所有政府部門、商業公司、民間團體均參與了大屠殺的相關事宜。其他受害的非猶太群體包括波蘭人、其他斯拉夫人、蘇聯平民及蘇聯戰俘、羅姆人、共產黨人、同性戀者、共濟會成員、耶和華見證人及身心障礙者[7][8][9]。德國與德國佔領區有近42,500個設施用於集中關押受害者,將其作為奴隸勞工使用,對其進行屠殺或其他反人權活動[10]。參與執行大屠殺的總人數估計超過200,000人[11]。
迫害與屠殺分階段進行,最終發展為「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對歐洲猶太人進行集體滅絕。最初德國政府通過法案(如《1935年紐倫堡法案》)以將猶太人自社會中排除出去。1933年起納粹開始建立一系列集中營,而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開始建立猶太區。1941年,德國佔領蘇聯在東歐的大片領土,開始廣泛獲取新領土,別動隊在這些區域屠殺了近兩百萬猶太人、游擊隊員及其他群體,手段普遍為大規模射殺。至1942年年末,受害者普遍乘火車前往滅絕營,若能在旅途中倖存,則將於毒氣室中遭系統性殺害。這一狀況一直持續至1945年4月至5月歐洲戰場尾聲階段[12]。
猶太武裝抵抗運動規模相對有限。最大規模的抵抗運動為1943年的華沙猶太區起義,數千武裝貧乏的猶太人抵禦武裝黨衛隊時間長達四周。在東歐,約20,000至30,000猶太游擊隊員同納粹德國、其傀儡政權及軸心國盟國展開鬥爭[13][14]。法國猶太人加入法國抵抗運動行列,對納粹及維希法國政權開展游擊戰。戰爭期間猶太武裝起義超過一百次[15]。
證據顯示希特拉知曉並下達了對猶太人的屠殺命令。根據阿道夫·艾希曼、海因里希·希姆萊和約瑟夫·戈培爾等人的陳述,希特拉本人策劃了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而希特拉本人的陳述也顯示了他打算屠光猶太人的意圖。[16]
命名起源

大屠殺「Holocaust」一詞源自希臘文「Holókauston」(燔祭),指將動物作為祭品獻給神靈,意為動物的「全部」(olos)被「燒毀」(kaustos)。[18]英語中以「Holocaust」代指大屠殺已逾數百年[19]。在二戰之前,「Holocaust」曾被丘吉爾用來指代一戰期間鄂圖曼帝國對亞美尼亞的大屠殺。1933年,這一詞語被用於形容納粹的焚書行徑,此為這一詞語首度用於形容納粹。[20]自1960年代起,該詞轉而被學者及流行作家用來特指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行為[19]。1978年後,電視連續劇「Holocaust」將該詞在大眾中普及開來。[21]
聖經詞彙「Shoah」(希伯來語:שואה,或Sho'ah、Shoa)意為「浩劫」,並早在1940年代成為希伯來文中成為大屠殺的同義詞,特別是在歐洲和以色列。[22]「Shoah」被猶太人引用是出於許多原因,神學中「holocaust」一詞含有貶義,同時該詞特指希臘當地的習俗。[註 1]意第緒語中稱為「חורבן」(Churben 或 Hurban),源自希伯來語,原意是指耶路撒冷神廟的毀滅。納粹屠殺的倖存者稱大屠殺為「der letster khurbn」(最近一次的毀滅),意即此次屠殺不過是猶太歷史中最近一次的苦難。[20]
納粹使用委婉語「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來描述該種族滅絕政策,並使用「不配活着的生命」來代指受害人,並以此來證明自己行為的正當性。
特點

邁克·貝倫鮑姆寫道:「德國變成了一個『種族滅絕之國』。[23]……國家所有複雜的機構都參與了屠殺。牧區教堂和內政部提供出生記錄、告發猶太人;郵局寄送放逐令和剝奪國籍令;財政部沒收猶太人財產;德國公司解僱猶太工人、終止猶太股權;大學拒絕錄取猶太學生、否定猶太文憑、解僱猶太院士;政府交通官員準備去往集中營的火車;德國藥廠測試毒藥;公司為火葬場競標;遇害人明細則使用德國IBM公司製造的打孔機,提供了屠殺的詳細資料;當犯人進入死亡營時,他們被迫繳納所有個人財物;德國國家銀行協助將從受害者那裏盜取的財產透過秘密賬戶來洗錢……在這些加害者的眼中,《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是德國的一個偉大成就。[24]」
歷史學者掃羅·弗里德蘭德寫道:「整個德國和歐洲沒有一個社會群體、宗教組織、學術組織或專業協會表示出自己對猶太人的支持。」[25]他寫道,一些基督教堂稱「皈依」的猶太人也應該被劃入這一群體,但在一些程度上被限制。弗里德蘭德稱這些都使得大屠殺富有獨特的性質,因為其反猶政策被實施時,沒有遇到任何干預,如在現代社會中工業組織、小微企業、宗教團體或其他利益集團、遊說組織的抗議。[25]
其它的種族滅絕主義是實用性的,即佔領土地,控制資源。以色列歷史學家耶胡達·巴爾稱:
大屠殺的基本動機是純粹的意識形態,植根於納粹的幻想世界,即猶太人密謀控制世界,反對雅利安的征途。這樣的屠殺行動是完完全全來自神話、幻想、抽象、非實用性的意識形態,是空前絕後的——而它的執行卻是十分理性,十分實用主義的。[26]
德國歷史學家埃伯哈德·傑克爾在1986年寫道了大屠殺的獨特性質:
從來沒有一個有責任心的國家領袖使用其權威,來決定並宣佈某個特定人群,包括所有年齡段、婦女、兒童、嬰兒,都應該被迅速地清除掉,並使用了整個國家一切可能的力量來執行這種暴行。[27]
1939年中東歐有700萬猶太人,其中500萬猶太人在那裏被屠殺,其中包括波蘭佔領區的300萬,以及蘇聯的100萬人。數以萬計的猶太人死在了荷蘭、法國、比利時、南斯拉夫、希臘。萬湖會議召開是為了謀求最終解決方案,納粹在此試圖將屠殺擴散到英國,以及其它中立國家,如愛爾蘭、瑞典、土耳其、葡萄牙、西班牙。[28]
有三到四個猶太裔祖父母的人都被殺無赦。在其它種族滅絕政策中,人們可以通過改宗或同化來躲過一劫。這對於猶太人來說不適用,[29]除非他們的祖父母在德意志第二帝國建立之日(1871年1月18日)前放棄猶太教。所有有近期猶太親屬的人,都會在納粹的控制區遇害[30]。
使用毒氣室、進行系統化的種族滅絕行動是大屠殺的一個特徵,這是在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從來沒有一個地方如此地公開地進行大肆處決。這些滅絕營包括奧斯威辛集中營、海烏姆諾滅絕營、貝爾賽克滅絕營、 馬伊達內克滅絕營、索比堡滅絕營、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瑪麗·特羅斯特內茲滅絕營、亞塞諾瓦茨集中營。
納粹屠殺的另一大特點大量使用人類作為「醫學」實驗品。勞爾·海爾堡(Raul Hilberg)的文獻指出「就納粹黨員人數來說,德國醫生較之其它專業更加高度納粹化。」他們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達豪集中營、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薩克森豪森集中營等地進行人體實驗。[31]
最為臭名昭著的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約瑟夫·門格勒醫生。他將實驗對象放入壓力室,在他們身上做藥物實驗、冷凍實驗,通過向兒童眼睛裏注射化學品以改變其顏色,以及其它各種截肢等手術。[31]他所做的一切已經不可能被全部知曉,因為檔案被送往威廉皇家學院,後被奧特馬爾·馮·費許爾醫生銷毀。[32]倖存者在之後講述了相關的噩運。
他在羅姆兒童身上進行了大量的實驗。通過給孩子們糖果和玩具,他將孩子們帶到毒氣室裏。孩子們會叫他「門格勒叔叔」。[33]維拉·亞歷山大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囚徒,負責照料50對羅姆雙胞胎,他回憶道:
我記得一對特別的雙胞胎:吉多和艾娜,大概四歲。一天,門格勒將他們帶走。當孩子們回來時,情況十分恐怖:倆人背靠背地被縫在了一起,好像連體雙胞胎那樣。傷口出現感染,不停地流膿。孩子們晝夜哭喊。他們的母親——我記得她名叫斯特拉——給孩子們注射了嗎啡,以便幫他們了結痛苦。[34]
發展與執行
总结
视角


耶胡達·巴爾、勞爾·海爾堡、路西·達維多維奇認為自中世紀以來,德國社會和文化就充斥着反猶主義,而納粹死亡營與中世紀少數族群迫害有意識形態上的直接聯繫。[36][37][38]包括馬丁路德也是反猶主義的推手。[39][40]
十九世紀下半葉,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和保羅·迪·拉加爾德在德國和奧匈帝國推動了民族主義的本土運動。這個運動使用了一種偽科學,即使用從生物學角度出發,將猶太人視為與雅利安民族征服世界的對頭。[41] 民族主義運動襲承了基督教反猶觀點,但不同的是,後者將猶太教視為一種宗教,而民族主義運動則將猶太人視為一個民族。[42]
1895,在德意志帝國議會前,民族主義領袖赫爾曼·艾爾沃特稱猶太人是「掠食者、霍亂桿菌,出於德國人民的利益應該清除他們。[43]」1912年,泛德意志聯盟領袖海因里希·克拉斯在他的暢銷書《如果我是皇上》(Wenn ich der Kaiser wär)中呼籲應取消所有德裔猶太人的國籍,將其打回外僑(Fremdenrecht)身份[44]。克拉斯同時呼籲,猶太人應該排除在一切德國生活之外,不許擁有土地、擔任公職、或從事新聞、金融、自由職業等工作。[44]克拉斯將猶太人定義為任何在1871年德意志帝國成立之日皈依猶太教的人,或是有一個猶太祖父母的人。[44]
在德意志帝國,民族主義及其種族主義的偽科學十分普遍,被受到良好教育的專業階層廣泛接受,[45]特別是在民族不平等的意識形態上得到認可。[46]雖然,民族主義黨在1912年的議會選舉時遭到失敗,但反猶主義被所有主流政黨所襲承。[45]1920年,作為民族主義運動的衍生派系——納粹黨成立了,並將他們的反猶主義傳承了下來。[47]就一戰後德國的局勢,德國歷史學家漢斯·蒙森在1986年的稿件中寫到:
如果某人堅持以孤立的角度來強調無可爭辯的重要關係的話,那麼從希特拉的世界觀到奧斯維辛的產生過程上,他不應該過度牽強,因為前者的態度絕不是什麼原創之舉... 對猶太人的滅絕政策不是一朝一夕的,也不是希特拉和他的同黨們的專利。從納粹黨那邊可以順藤摸瓜到「德國種族保護和反抗聯盟」那裏,後者則由泛德意志聯盟賦予了生命。[48]
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德國的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加之國家福利的不斷提升,烏托邦就要實現的氣氛在社會上廣為流傳。[49]於此同時,種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人種改良世界觀宣稱一些人種在生理上優於另一些人種。[50]歷史學家迪特列夫·克特稱「浩劫」不單單是源自於反猶主義,而是一種「激進的累積」,是「許許多多小支流」匯集成為「大江」,並最終導致種族的滅絕行動。[51]在一戰後,戰前的樂觀主義讓位給了幻滅,即德國官方發現許多社會問題無法解決,不得不強調留存生理上「優良」的種族,讓另一些「低劣」的滅絕。[52]
大蕭條所帶來的經濟問題使得許多德國醫療機構鼓吹以安樂死讓那些生理與心理上「無可救藥」的人先死去,用省下來的錢來救濟尚存希望的患者。[53]在1933年納粹政府上台時,德國社會也出現了相對應的政策:拯救「有價值的」種族,消滅「可憎的」社會渣滓。[54]
希特拉將自己對猶太人的仇恨進行了公開化。在他的著作《我的奮鬥》中,他預示了自己的打算:將猶太人從德國政治、學術、文化等領域驅逐出去。他沒有提到自己要屠殺他們,但據報道稱希特拉在私底下將自己的企圖表現的更加赤裸。早在1922年,據說他與當時擔任記者的前少校軍官——約瑟夫·黑爾(Joseph Hell)談及自己的觀點:[55]
一旦我掌了權,我的首要任務將是滅除猶太人。只要能力許可,我就把絞刑架稱排地架起來——比如,從瑪利亞廣場一直架到慕尼黑——只要交通許可的話。然後,這些猶太人將不分老幼地被絞死,並一直掛在那裏,直到屍體變臭為止;只要衛生條件允許,他們將一直被掛在那裏。一批被取下,另一批就立即跟上,直到慕尼黑的最後一個猶太人斷了氣為止。其它城市也要如此效法,精確地統一方式,直到全德國都將猶太人清除乾淨為止。
莫姆森稱在德國有三種類型的反猶主義:[56]
人們應當區分德國保守派的文化反猶結症——其主要在德國軍官和政府高層中流傳——反東方猶太主義,以及民族主義的反猶情結。保守派的功能各異,正如舒拉米特·霍爾科夫所指出的那樣,是一種「文化符號」。這種德國反猶主義在日後起了重要作用,使得功能性精英迴避了反猶運動的影響。因此,對於猶太人受到迫害一事上,帝國政府中的將軍、政黨領袖無一人出面干預。這在希特拉對蘇聯發動的「種族滅絕戰爭」來說再適用不過。
在德國,另一種反猶保守勢力是羅馬天主教,它的冷漠導致教徒們對不斷升級的大迫害無動於衷。天主教最著名的抗議是針對安樂死的,而就大屠殺而言他們竟然一聲不吭。
第三種,也是最殘忍的反猶主義是所謂的民族主義反猶運動,或種族主義;它強烈鼓吹使用暴力。不管怎樣,人們必須注意,甚至是在1938-1939年間,希特拉都一直通過使用移民的方式來排斥德國猶太人;此時,並沒有出現明確的屠殺概念。然而,這並不意味着納粹在其它地方吝惜下狠手,侵犯猶太人、猶太商鋪、機構,這些都是明擺着的。然而,直到戰爭打響的第二年,正式的屠殺活動才浮出水面。這是「預留」計劃失敗之後跟進的。當然,這並不代表上述方案沒有包含致命因素。
| “ | 一個有尊嚴的國家在任何尺度上都不能允許將最高級別的活動讓位給異族出身的種族……就異族出身人種對比大眾人口來說,允許前者的過高比例等同於接受另一種族的優越性,這是必須被推翻的。[57] | ” |
| ——1933年4月27日,《德意志匯報》 | ||
自第三帝國誕生之日起,納粹領袖們就鼓吹創立一種「民族共同體」制度,後來納粹政權將國民分成兩大類,一類是「民族同志」,屬於民族共同體的一份子;另一類是「社會異類」(Gemeinschaftsfremde),他們不是民族共同體的成員。納粹將打壓對象分為三類:一種是「種族」敵人,如猶太人、吉卜賽人,他們因為「血統」的關係被視為敵人;政治上的異議分子,如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者,基督徒和反動派,他們被視為叛逆的「民族同志」;道德墮落分子,如同性戀、懶漢、慣犯等,也被列為叛逆的「民族同志」當中。[58]後兩部分人被送進集中營進行「再教育」,以將其最終轉化為民族共同體的成員。有許多道德墮落分子被視為「基因低級」而不得不接受絕育。[58]
根據定義來講,「種族」敵人如猶太人永不可歸入民族共同體當中;他們必須完全從社會中清除出去。[58]德國歷史學家克特寫道納粹黨的「目標是建立烏托邦式的民族共同體,進行全方位的警視監督,所有試圖反抗的行為,或類似的跡象、意圖,都將受到殘酷的打擊。」[59]克特引用了1944年《社會異類辦法》(Treatment of Community Aliens)中的一些資料,揭示了納粹的些許社會政策:「公民…表明自己的努力無法達到國家社會的最低要求的話,將會被置於警視監督之下,如果這樣都不能奏效的話,就把他們送入集中營。[60]」

在1933年3月的帝國議會選舉當中,納粹強化了對敵手的暴力措施。他們與地方當局一道設立法外集中營,關押異議人士。1933年3月9日,達豪集中營率先上線。[61]集中營最初是用來關押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用的。[62]其它的早期監獄——如衝鋒隊和黨衛隊的地下室、倉庫——在1934年中期被加固,在城外改建成營地,由黨衛隊集中管理。這些營地最初是用來清除那些不願服從民族共同體的德國恐怖分子用的。[63]這些被送入營地的包括「可教育」的分子,即可能被歸入「民族同志」的人,和「生理墮落」的人,後者將處以絕育,並被永久關押;之後,營地多採取苦役,即不停地勞動,直至疲勞倒地為止。[63]
整個1930年代,猶太人在法律、經濟、社會權益上都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限制。以色列歷史學家弗里德蘭德寫道,在納粹看來,德國的力量來自「血統的純正和神聖的德國土地。」[64]1933年4月1日,一個次全國反猶集會進行抵制猶太商貨運動,原計劃持續一周,但由於缺乏大眾支持,進行了一天後就不了了之。1933年,一系列包涵雅利安人字眼的法案被通過,將猶太人從關鍵職位上排除出去:如第三帝國的第一道反猶主義法案——《專業行政工作恢復法案》以及《醫師法》(Physcians' Law)、禁止猶太人擁有農莊,或從事農業工作《農業法》(Farm Law)等。
猶太律師也被停職,在德累斯頓,猶太律師和法官被拖出辦公室,並被毆打。[65]在前總統保羅·馮·興登堡的要求之下,希特拉頒佈特令,准許一次大戰的猶太裔老兵、或有父子服役過的公務員留在其職位上。希特拉在1937年取消了這項特令。根據《預防學校人數過多法案》(Law to Prevent Overcrowding in Schools),猶太人被學校和大學開除,不能參加新聞報社協會,擁有報社,或成為報社編輯。[64]
在1933年7月,《遺傳疾病後裔防治法》強迫對「劣種人」進行生理絕育。這種優生政策催生了200多個「遺傳健康法庭」,有超過400,000人被迫絕育。[66]

1935年,希特拉頒佈了《紐倫堡法案》,其中的《德國血統和榮譽保護法》(Gesetz zum Schutze des deutschen Blutes und der deutschen Ehre)即禁止猶太人與「雅利安人」結婚或發生性行為,剝奪猶太人的德國國籍和國民基本權利。就「血統法案」而言,希特拉解釋稱其「試圖通過法律途徑解決這一問題,如果失敗的話就將問題交由納粹黨,啟用最終解決方案。」[67]「最終解決方案」是納粹對屠殺猶太人的委婉語。1939年1月,他在公開演說中稱:「如果猶太人在歐洲內外的跨國金融再次得逞,將國家拖入另一場世界大戰的話,那麼結果將不是全球的布爾什維克化或是猶太人的勝利,而是他們在歐洲的滅絕之日。」[68]該演講被1940年的納粹宣傳電影《永遠的猶太人》引用,其目的是提供一個從歐洲清除猶太人的理性藍圖。[69]
最早逃離納粹迫害的是猶太人中的知識分子,如哲學家瓦爾特·本雅明於1933年3月18日逃到巴黎、小說家利翁·福伊希特萬格則去了瑞典、指揮家布魯諾·瓦爾特也被警告若於柏林愛樂樂團演出,該建築將會被縱火,因此4月6日的《法蘭克福報》報導了瓦爾特和他的同事奧托·克倫佩勒被迫流亡的訊息,寫述民眾的情緒已經被「猶太藝術清算者」所挑起,而政府也無法保護他們的安全[70]科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也被威廉皇家學院和普魯士科學院開除,國籍也被取消,他於1933年1月30日訪問美國,後再前往比利時奧斯滕德,從此也再無踏上德國領土,他稱這些迫害事件是「集體性的神經病」。[71]當德國於1938年吞併奧地利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他的家人從維也納流亡英國。掃羅·弗里德蘭德寫道當普魯士藝術學院的榮譽主席馬克斯·利貝曼辭職時,沒有一位同事表示出一絲的同情,兩年後,當他去世時,依然在亡命天涯。1943年,當警察抬着擔架來到他85歲、臥床不起的遺孀那裏時,後者通過服用過量的巴比妥酸鹽來一眠不醒,以免被他們帶走。[71]
水晶之夜又名「碎玻璃之夜」。1938年11月7日,猶太青年赫佐爾·格林斯潘在巴黎暗殺了德國外交官恩斯特·馮·拉特。[72]這起事件成了納粹政府用來跳脫針對以法律迫害猶太人的範圍,將其升級為大規模物理性衝突的藉口。其所聲稱的「公憤」實際上也是納粹政府在背後煽動、由衝鋒隊執行的一波迫害行動,範圍包括德國、奧地利、蘇台德區。[72]這些迫害行動被稱之為「水晶之夜」(即碎玻璃之夜,指被打破的猶太商店櫥窗玻璃有如水晶)或「十一月迫害」。猶太人遭到襲擊,他們的財產被洗劫,超過7,000個商鋪和1,668座猶太教堂(幾乎是德國境內的全部教堂)被掃蕩。
官方公佈的死亡人數為91人,事實上應該遠高於此。30,000人被送往集中營,包括達豪集中營、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奧拉寧堡集中營[註 2],他們被關押數週後被釋放,前提是答應在近期離開德國,或將財產上交納粹黨。[73]1938年11月11日,納粹政府通過了《猶太人持有武器禁令》(Verordnung gegen der Waffenbesitz der Juden),禁止猶太人持有槍支或其武器。[74]猶太人被集體要求賠償迫害所造成的財物損失,價值將近幾十萬德國馬克,並要繳納超過十億馬克的「贖罪稅」。[72]在這一輪迫害之後,猶太出境移民加速,而在德國的猶太公共生活不復存在。[72]

在戰爭打響之前,納粹考慮過將徳裔猶太人從歐洲驅逐出去。希特拉曾於1938年同意了將數以千計的猶太人趕出德國的「沙赫特計劃」(Schacht),標誌了在當時德國政府還未進行系統化的屠殺行動。[75][註 3]
有的計劃試圖將猶太人送往前德國殖民地重新安置,如坦噶尼喀、西南非,以便幫助收復因《凡爾賽條約》而失去的這些地區。然而這一計劃被希特拉否決,他表示絕不能讓「沾有德國英魂鮮血的土地被德國最大的敵人所玷污。」[76]另外還有其它外交策略嘗試將猶太人送往其它地區,如前英法殖民地。[77]幾個被考慮過的地點包括英屬巴勒斯坦[78]、羅德西亞[79]、埃塞俄比亞[78]、法屬馬達加斯加[78]、澳大利亞[80]等地。
在上述地區中,馬達加斯加的討論最為激烈。萊因哈德·海德里希稱這項「馬達加斯加計劃」是「地域性的最終解決方案」,該地位置偏遠、島上的環境惡劣,容易導致死亡。[81] 1938年,計劃被希特拉批准,重新安置計劃由阿道夫·艾希曼的部門進行執行,並於1941年大屠殺開始時終止。回頭看來,雖然計劃最終不了了之,但它卻為大屠殺在心理上鋪墊了道路。[82]1942年2月10日,「馬達加斯加計劃」被宣佈廢止。德國外交部的官方解釋是由於與蘇聯的戰爭爆發,猶太人將會被「送往東方」。[83]
納粹政府還有提出一些另類方案,如將歐洲猶太人轉送到西伯利亞地區。[84]在納粹的重新安置計劃中,巴勒斯坦是唯一一個有了顯著成果的地區。1933年,德國猶太人復國主義聯盟與納粹政府達成了《哈瓦拉協定》,60,000名徳裔猶太人將從德國送往巴勒斯坦,並得到了一億美元的轉移款項,然而此計劃因二戰爆發而不了了之。[85][86]
| “ | 我的唯一要求就是讓猶太人消失。 | ” |
| ——漢斯·法郎克,波蘭總督府首長[87] | ||
納粹德國於1939年入侵波蘭,幾世紀以來,波蘭處處都有猶太人居住,在德軍入侵當時約200萬人,占人口總數的9%左右,這加強了德國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急迫性。
海德里希建議將主要城市中所有波蘭裔猶太人送入隔離區,讓他們為德國軍工服苦役。隔離區處在城市鐵路交匯處,海德里希表示這將更容易控制(猶太人),並(方便)之後將他們處理掉。[88]艾希曼後來在1961年被以色列法庭問詢時,他表示之後的「處理」就是「物理性的屠殺」。[89]
9月,希姆萊任命海德里希為黨衛隊國家安全部的部長。這個部門有七個機構組成,包括黨衛隊保安處和蓋世太保。[90]他們負責監督黨衛隊在波蘭的工作,並執行海因里希報告中處置猶太人的方案。第一次有組織的屠殺為「坦能堡行動」,由自衛團執行。猶太人之後被趕入遍佈於波蘭總督府的中心地帶隔離區,由弗里茨·紹克爾管理的帝國勞動部監督服苦役。數以千計的人因虐待、疾病、飢餓、精疲力盡而倒斃,但至此仍沒有出現系統化屠殺項目。但毋庸置疑的是,納粹將服苦役作為了一種滅絕方式,甚至有了專有名詞——「死於苦役」(Vernichtung durch Arbeit)特指此事。
很明顯,到1941年時,黨衛隊領導層已經決意要着手制定政策來屠殺所有德軍佔領區內的猶太人。在當時,納粹統治內部對此仍有反對聲音,而該反對聲音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而非出於人道考量,如身兼空軍總司令和經濟部長的赫爾曼·戈林元帥即是主要的反對者之一,當時他負責統籌德國的所有軍工事務與經濟部門,認為在德軍入侵蘇聯前,波蘭總督府內數量龐大的猶太勞工(超過100萬壯勞力)彌足珍貴,浪費可惜。

1939年9月28日,德國以《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和蘇聯達成協議,控制了波蘭盧布林地區以及瓜分了立陶宛[91],之後根據「尼斯科計劃」建立了盧布林保留地。保留地由阿道夫·艾希曼設計,後者負責將德國、奧地利、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等地區的猶太人驅除乾淨。[92]三周後的1939年10月18日,他們將第一位猶太人送往盧布林地區。第一列滿載猶太人的火車從奧地利、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駛出,[93]到1940年1月30日,總計有78,000名猶太人從德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轉送到盧布林。[94]1940年2月12和13日,波希米亞猶太人被送至盧布林保留地,使得波西米亞地方官弗朗茨·許威德-科堡首先宣佈他的省份「沒有猶太人了」。[95]1940年3月24日,戈林暫停了「尼斯科計劃」,並在4月底將其完全放棄。[96]在尼斯科計劃被終止時,總計有95,000猶太人被送往尼斯科,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中途因飢餓而死。[97]
1940年7月,維持波蘭總督府龐大的人群變得越來越困難,希特拉暫時叫停了安置計劃。[98]
1940年10月,大區長官約瑟夫·布克爾和羅伯特·海因里希·瓦格納督辦了「布克爾行動」(Operation Bürckel),將猶太人從他們的省份和被帝國兼併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趕入尚有餘地的法國。[99]只有混血的猶太人沒有被驅逐。[99]1940年10月22-23日晚,有6,500名猶太人被布克爾行動驅逐,並僅僅給予了至多兩小時的警示時間,就被押解起來。9輛滿載猶太人的列車在「沒有對法國官方有任何告知」的情況下長驅直入,後者對此怏怏接受。[99]被安置人員不得攜帶任何物品,財物則全被德國官方沒收。[99]德國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則將維希政府的抗議以「最為拖拉的方式」進行處理。[99]結果,被布克爾行動驅逐的猶太人被維希政府拘禁在環境惡劣的居爾(Gurs)收容所、里韋薩爾特營、米勒斯營,等待機會返回德國。[99]
1940到1941年間,在德控波蘭地區對猶太人的屠殺行動不斷,將猶太人向波蘭總督府的輸送持續。德國,特別是柏林地區的猶太人清除工作直到1943年才完全告終(在此期間,許多猶太人可以通過躲避來苟延)。到1939年12月,總計有350萬猶太人被送入擁擠的波蘭總督府地區。
1940年,德國佔領了丹麥、挪威、荷蘭、盧森堡、比利時、法國;1941年,德國及其盟友又佔領及肢解了南斯拉夫、希臘。反猶主義被輸送到這些國家中,並根據當地政治局勢的不同而在程度和節奏上有所不同。猶太人被迫離開經濟和文化生活,並受到各種苛刻律令的壓制,但在1942年之前,大規模的物理驅逐還沒有開始。德國的傀儡政權維希法國積極配合對法裔猶太人的迫害。德國的盟友意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芬蘭也受到相應壓力,被迫制定反猶政策,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直到被催促時才執行。在戰爭中,有900名猶太人、300羅姆人從貝爾格萊德的班吉卡(Banjica)集中營逃離,這主要是由塞爾維亞共產黨人、保皇黨人和其它抵抗運動者組織的。德國及意大利的傀儡政權克羅地亞獨立國則積極自發地迫害猶太人,並與1941年10月10日頒佈了《將猶太財產和公司國有化法令》。
| 「 | 我根本一點都不相信愚蠢的反猶理論,制定種族法的原因只是政治因素而已 | 」 |
| ——貝尼托.墨索里尼,意大利首相[100] | ||
在希特拉德國的壓力下,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在1938年時就制定了針對意裔猶太人的意大利種族法。儘管如此,意大利國內的反猶情緒比納粹德國低很多,因此對於當時猶太人來說,意大利控制下的地區比德國控制下的地區更安全[101]。意大利也有集中營供猶太人,但法西斯黨政府只將他們當作政治犯看待,集中營的猶太人享有基本的生活質素和建立組織的自由[102],和德國的集中營完全是天壤之別。1941年克羅地亞獨立國在南斯拉夫的廢墟中建立後,大量猶太人為躲避克羅地亞東部的德國駐軍和烏斯塔沙政權逃亡去意大利直接控制的地區(烏斯塔沙不能在亞得里亞海沿岸地區部署任何軍事組織),而且克羅地亞是意大利的保護國、所以只能聽命其宗主國,意大利駐軍知道烏斯塔沙的種族滅絕行為因此有向猶太人提供保護。德國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曾向墨索里尼抱怨說:「意大利軍方……缺乏對猶太人問題的正確理解。」[103]
烏斯塔沙的恐怖統治及迫害包括猶太人在內的種族加劇了抵抗運動的勢力。1941年8月意大利王國決定重新將克羅地亞獨立國西部軍事化,並派兵去鎮壓南斯拉夫游擊隊,意大利軍隊也順便關閉了兩個集中營,被關閉分別是亞多夫諾集中營[104]和帕島集中營[105],因為這些集中營過於反人類和不人道。位於維泰茲的一所集中營會有意大利外交代表探訪並查找有沒有意大利公民在集中營,如果有該名受害者會受到保護。同樣地在意大利控制下的阿爾巴尼亞、希臘國、黑山軍政府及法國意佔區的所有猶太人皆受到保護[106]。直到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後,本土及其佔領地被德國接管,對意大利保護下的猶太人的迫害正式開始。
匈牙利早在1920年由霍爾蒂攝政成立時就立了一些對匈牙利裔猶太人不平等的政策,直至1944年匈牙利因企圖和盟軍停戰而被德國佔領時,匈牙利國內的猶太人並未受嚴重的迫害。1944年匈牙利箭十字黨政府開始運送猶太人到德國集中營。
羅馬尼亞是其中一個積極迫害猶太人的德國盟友。1940年總理安東內斯庫上台執政後,法西斯組織鐵衛團開始在國內大量迫害猶太人,即使鐵衛團在41年因政變失敗而被安東內斯庫總理消滅也未停止。羅馬尼亞軍隊在蘇德戰爭時期在敖德薩及雅西屠殺了大量猶太人(1941年敖德薩大屠殺)。1942年夏羅馬尼亞政府開始大量運送猶太人去德國及德國佔領地的集中營。
保加利亞於1941年有針對猶太人的政策,在德國壓力下,保加利亞政府運送居住在保加利亞佔領區的猶太人去特雷布林卡滅絕營。1943年,在東正教教會抗議下,保加利亞沙皇鮑里斯三世停止了運送猶太人去德國集中營。
1942年芬蘭在德國壓力下運了150-200名非芬蘭裔猶太人去德國,在民眾反對下,最終芬蘭政府只運了8名非芬蘭裔猶太人去德國集中營,只有一名在戰後活下來。

第三帝國於成立之初即創建了集中營。起初,集中營只用於關押犯人,儘管死亡率高達50%,但並非專用於屠殺。1939年後,集中營越來越多地處死猶太人、戰俘,或讓其苦役、不給飯吃、虐待等等。[107]據估算,德國在歐洲佔領地建立起約15,000座集中營。[108][109],直至1942年,德國僅在波蘭境內就建立了6所專司大規模屠殺的大型集中營。新集中營主要關押猶太人、波蘭知識分子、共產黨人、羅姆人、辛特人。這些囚犯通過鐵路運送,其惡劣的環境導致許多人還沒到目的地就一命嗚呼。
苦役是一種系統化的滅絕政策——囚犯會被處以苦役、勞動致死,或是竭力工作後,被送往毒氣室或槍決。[110][111]奴隸們會被用於軍工製造,如在米特堡-朵拉集中營生產V-2火箭,或是茅特豪森-古森集中營生產其它武器。
進入時,一些集中營為囚犯印製臂章。[112]勞力的工作時間表為12-14小時輪替制。有時,囚犯們的點名就需要幾個小時,導致許多人暴曬致死。[113]


在入侵波蘭後,納粹設立了猶太隔離區,囚禁猶太人和一些羅姆人,並最終將他們送往滅絕營。1939年9月29日,海德里希在給別動隊頭子的信中命令建立委員會。[114]每個隔離區由一個猶太居民委員會管理,德方任命猶太社區領袖,後者負責隔離區的日常運轉,包括分發食物、水、取暖、設立庇護所等。委員會的基本策略是將損失最小化,與納粹合作,接受日益殘酷的虐待,懇求更好和更仁慈的待遇。[115]委員會被要求安排人員,將他們送到滅絕營去,[116]因此,在制定下一批離去的人員列表時,每一位猶太委員會成員都面臨着勇氣與品質的考驗。猶太委員會成員嘗試了拖延、賄賂、阻撓、求情、辯論等各種方式,直到逼不得已為止。有的如哈伊姆·盧特考斯基認為他們的責任是拯救「能夠」被救援的猶太人,這也意味着有部份人也將不得不被犧牲掉;反之,也有信仰邁蒙尼德思想的猶太人堅持除非有猶太人犯了重罪,否則一個人也不交出去。舉例來說,利沃夫的猶太委員會領袖約瑟夫·帕爾納斯博士拒絕為納粹編訂名單,結果被後者所槍決。1942年10月14日,別廖扎的猶太委員會拒絕與納粹合作,全體成員自盡而亡。[117]
德方利用委員會的重要作用來對隔離區猶太人進行迫害的殺戮:一位官員強調「猶太委員會的權威必須在任何情況下得到支持和強化」,[118]「任何不服從委員會指令的猶太人都被視為破壞者。[116]」當雙方合作破裂,如華沙隔離區的猶太抵抗組織取代了委員會的地位時,德國對局勢失去了控制。[119]
華沙隔離區是最大的隔離區,有約380,000人;羅茲隔離區位列第二,有約160,000人。在現實中,隔離區人滿為患,邁克·貝倫鮑姆將其形容為「緩慢、被動的謀殺」工具。[120]雖然華沙隔離區的人口占波蘭首都總人口的30%,但它在面積上只佔城市的2.4%,也就是說平均每個房間裏住9.2人。[121]在1940到1942年間,飢餓與疾病,特別是傷寒奪取了數以成百上千人的生命。1941年,有43,000人在華沙隔離區喪命,[121]比例超過十分之一;1942年,有超過一半的人在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死亡。[120]1942年7月19日,希姆萊開始下驅逐令,三天後的7月22日,驅逐從華沙隔離區開始;在之後的52天、到12月12日為止,有300,000乘坐火車離開華沙,前往特雷布林卡滅絕營。很多隔離區一下子變為空城。1942年12月,波蘭東南方的拉克瓦發生了首次的隔離區武裝起義。1943年時又有幾個規模稍大的隔離區也出現了類似的武裝起義,例如華沙和比亞韋斯托克隔離區,但猶太人的抵抗很快地就被擁有壓倒性優勢的納粹軍隊所鎮壓,倖存者不是被處決就是被送進滅絕營中。[122]
二戰中,一系列對猶太人的迫害在當地出現,有的受到了納粹德國的煽動,有的則是自發形成的。例如德國的盟友羅馬尼亞王國在1941年6月30日在境內的雅西爆發了大規模反猶迫害行動,約有14,000名猶太人被羅馬尼亞居民和警察打死。1941年7月,波蘭耶德瓦布內境內的波蘭人在德方秩序警察的目睹下將300名猶太人關入穀倉、放火燒死,此前該地也另有40名猶太人被德國人處死。這些事件經過由國家記憶研究院於2000至2003年透過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對遺骸的發掘考證而得知,也因此推翻了早期遇難者估計人數較多的傳聞。[123][124][125][126][127]1942年1月,德國另一位盟友匈牙利王國也在其佔領區諾維薩德內屠殺了3000名猶太人及塞爾維亞人,一些猶太人被匈牙利皇家陸軍運去德國在塞爾維亞救國政府的集中營。
总结
视角

1941年6月,納粹德國進攻蘇聯,屠殺猶太人的行動進入了新階段。在德軍佔領立陶宛後,大屠殺的規模加劇了。在年終前,立陶宛全國近80%的猶太人被殺害,約有220,000人罹難。[128][129]蘇聯領土在1942年早期被侵佔,包括白俄羅斯、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烏克蘭、以及列寧格勒-莫斯科-羅斯托夫以西的俄羅斯。這當中有約300萬名猶太人,其中包括在1939年逃離波蘭的人。
一些蘇聯被佔領土上的當地居民對屠殺號召做了積極響應。[130]在立陶宛、拉脫維亞、和西烏克蘭,當地居民從德國人一道積極參與對猶太人的屠殺活動。[130] 拉脫維亞人阿拉沙·科曼多是一個協助人員的例子。[130]在南方,烏克蘭人殺死了約24,000名猶太人。[130]另外,拉脫維亞人和立陶宛人從他們自己的國家出去,跑到白俄羅斯那裏殺當地的猶太人。烏克蘭總督轄區則建立集中營,為波蘭提供屠殺場所。[130]克羅地亞獨立國的法西斯組織——「烏斯塔沙」也積極執行迫害和屠殺,但歸根到底是德國人組織和引導這些當地人參與大屠殺活動的。[130]
很多大屠殺在公共場所進行,這與以往相比有所不同。[130]目擊證人稱這些屠殺活動包含了當地人的參與。[130]別動隊的屠殺活動常常以反游擊隊、打擊土匪為理由,但德國歷史學家安德烈亞斯·希爾格魯貝爾認為這不過是德軍的藉口,這些在俄羅斯發生的事情完全符合「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的標準。[131]希爾格魯貝爾堅持屠殺220萬手無寸鐵的男人、婦女、兒童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毫無道理可言,而德國將軍們稱別動隊在打擊游擊隊的託詞根本是在撒謊。[132]
德國國防軍與黨衛隊在反游擊隊和反猶太人的工作中彼此密切合作。[133]在1941年中期,黨衛隊騎兵旅赫爾曼·菲格萊因在「反游擊隊」普里皮亞季沼澤地殺死了699名紅軍士兵,1,100名游擊隊員和14,178名猶太人。[133]在行動前,菲格萊因命令將所有猶太成年人槍決,爾後將婦女而兒童趕入沼澤地。在行動後,指揮德國中央集團軍後衛部隊的馬克斯·馮·許恩克多夫將軍在1941年8月10日命令所有德國國防軍後衛部隊在反游擊隊的任務上效法菲格萊因,並於1941年9月24-26日與黨衛隊一道在莫吉廖夫組織了聯合演習,研究殺死猶太人的最佳方案。[133]演習的結果是警衛營第7連在一個叫金沙薩(Knjashizy)的小村子射殺了32名猶太人,軍官們對此美名其曰稱這是從人群中「篩查」游擊隊的方式。[134]第322營的戰爭日記上這樣寫道:
行動首先是在小村落中進行的「實戰訓練演習」(ernstfallmässig)。陌生人、特別是游擊隊員一個也沒有找到。在篩查過程中,發現了13名猶太人,27名猶太婦女和11名猶太兒童。結果,13名猶太人和19名猶太婦女在與保安部隊的聯合行動中被射殺。[134]


根據他們在莫吉廖夫演習中學到的東西,一位德國國防軍長官告訴他的部下:「有游擊隊的地方就有猶太人,有猶太人的地方就有游擊隊」。[134]在1941年11月24日的第24號令當中,第707師師長稱:
猶太人和吉卜賽人...已經得到命令,猶太人必須從這片國度上消失,吉卜賽人也必須清除乾淨。執行「大尺度」的猶太人方案不會是集團軍的任務。民政和警衛部隊將會負責此事,除非白魯塞尼亞的司令另有指令,或是他有剩餘的特別部隊,或是出於安全考慮必須進行集中處罰。當較小或較大的猶太人在中途被碰上,他們可以由分部清除,或是集中到臨近村落的隔離區,交由當地的負責人或保安處來處理。[135]
德國歷史學家尤爾根·福斯特是德國國防軍戰爭犯罪方面的專家,他認為德國國防軍在大屠殺上起了重要作用,並將罪過全部歸結到黨衛隊上,因此將德國國防軍視為被動的、不情願的旁觀者是錯誤的。[136]海爾堡則認為別動隊的指揮官們都是普通人,而絕大多數動手的是專業人士,有的甚至是知識分子。他們傾盡所學的一切技能,成為了高效的殺手。[137]
在蘇聯佔領地的大規模屠猶任務由黨衛隊的別動隊來完成,由海德里希統一指揮。1939年的波蘭屠殺尚存局限,但如今卻在規模上有所升級。別動隊A隊負責波羅的海地區,B隊負責白俄羅斯,C隊負責烏克蘭北部和中部,D隊負責摩爾多瓦、南烏克蘭克里米亞,並在1942年負責高加索地區。[138]
奧托·奧倫多夫在審判庭上稱:「別動隊的任務是保護軍隊後防,屠殺猶太人、吉卜賽人、共產黨人以及其它會對安全產生威脅的人員。」實際上,被害人基本上全是手無寸鐵的猶太平民(在整個行動中,別動隊連一個隊員都沒有犧牲)。到1941年12月,四分隊給出的成績分別是125,000人、45,000人、75,000人、55,000人——總計為300,000人——主要方式是在城鎮外執行槍決或扔手榴彈。1942年4月6日是逾越節的第二天,別動隊在烏克蘭皮里亞京屠殺了1,600名猶太人[139]。
在蘇聯佔領地上最為臭名昭著的是基輔外的「娘子谷大屠殺」,在1941年9月29-30日的單次行動中就有33,771名猶太人喪命。[140]軍政府長官少將弗里德里希·埃伯哈特,南方集團軍麾下的警察部隊總司令——弗里德里希·耶克爾恩和別動隊C隊司令奧托·拉施決意要消滅基輔內全部的猶太人。由黨衛隊、保安處和烏克蘭當地警方執行殺戮。雖然第6集團軍沒有直接參與,但他們在將基輔猶太人趕出城鎮,送入娘子谷上起了關鍵作用。[141]
周一,基輔的猶太人聚集在公墓,準備登上火車。由於人群龐大,大多數的男人、婦女、兒童都沒有來得及知道怎麼回事,就聽到機槍響起,無處可逃。人們被一群士兵驅逐,然後被射殺。一位卡車司機描述道:
他們一個接着一個地放下行李,然後脫下大衣、鞋子、外套、內衣… 當脫乾淨後,他們被帶到150米長、30米寬、15米深的谷中… 當他們到達谷底時,防護警察強迫他們躺在已經被射殺的猶太人身上… 屍體層層堆積。警方的射手過來,用衝鋒鎗射擊他們的脖頸… 我看到這些射手站在屍體層上,一個接着一個地射殺着… 射手會踏着屍體,走到下一個人旁邊,後者躺臥在地,射手對其行刑。[142]
1941年,希姆萊在明斯克目睹了100名猶太人在城鎮外的溝內被射殺,他的副手卡爾·沃爾夫在日記中寫道:「希姆萊的臉色變青。一塊兒腦漿濺到他的臉上,他拿出手絹將腦漿擦掉,然後嘔吐不止。」心情平復後,他向黨衛隊員訓話,稱執行任務時必須遵守「納粹黨的最高道德準則」。[143]

從1939年12月起,使用毒氣作為屠殺的新方式。[144]起初,毒氣罐被裝置成筒形,放入密閉的貨車中,用以處決療養院中的精神病人。作為T-4行動的一部分,它被廣泛用於波美拉尼亞、東普魯士、波蘭佔領區等地。[144]在薩克森豪森集中營,能處決多達100人的大毒氣車在1941年11月被使用,設備為發動機排氣裝置而不是筒形。[144]這些毒氣車在1941年12月被海烏姆諾滅絕營採用,其它15個則被別動隊用在了蘇聯佔領地上。[144]這些毒氣車由黨衛隊生產,並由黨衛隊國家安全部監督使用。毒氣車殺死了約500,000人,主要是猶太人、羅姆人和其它種族。[144]這些毒氣車被細心地監控着,在一個月的觀察後,報告指出:「三輛車被使用了97,000次,沒有出現一點故障。」。[145]
波蘭總督府的漢斯·法郎克表示需要研發更加新型有效的屠殺工具,而不是簡簡單單對這些人執行槍決。「我們應該更進一步,設計一些辦法來處決他們。」 這個問題時的黨衛隊實驗出大規模毒氣屠殺方式。克里斯蒂安·沃思(Christian Wirth)可能是毒氣室的發明人。
1942年1月20日,萊因哈德·海德里希在柏林郊區萬湖主持了萬湖會議,有15名納粹領袖,把包括一些國務秘書、政府高官、納粹黨領袖、黨衛隊官員以及其它制定與猶太人政策相關的政府部位領導人。會議最初的目的是討論「歐洲猶太人問題」的徹底解決方案。海德里希有意「在各個不同的佔領地區規劃出大規模屠殺. . . 作為希特拉下達的解決歐洲猶太人問題的答覆……為了確保執行,必須讓部委層級官僚知曉,並使其共同承擔執行這項政策的責任。」[146]
艾希曼所作的備忘錄副本被留存了下來,然而海德里希的指示是以「委婉語」的風格寫成,因此會議上的真實用語無從知曉。[147]海德里希在會議上的意見表明將把猶太人轉送至東方,代替之前的對外移民政策。這項政策不過是最終解決方案之前的一個臨時計劃,涵蓋了1100萬名猶太人,範圍不但包括德國,而且包括了世界上的其它主要國家,如英國、美國。[148]解決方案是毫無懸念的:「海德里希明確說明在『最終方案』階段,猶太人必須以苦役和大屠殺的方式全部殲滅。」[149]
官方稱猶太人在波蘭總督府有230萬人,匈牙利有8.5萬人,其它國家有110萬人,蘇聯500萬人,但200萬依然在未被控制的領土上。這樣,總計為650萬。他們將會用火車送至地處波蘭的「滅絕營」,然後立即被送入毒氣室。在一些營地,如奧斯維辛營,可以勞動的就先留下,然後再殺。戈林的代表,埃里希·諾依曼博士則帶走了一少部分人用於工業生產。[150]
伊恩·克肖在他1983的著作——《第三帝國公眾意見和政治異議》(Popular Opinion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Third Reich)一書中探討了巴伐利亞納粹時期的「日常歷史」(Alltagsgeschichte)。[154]就巴伐利亞人的大多數態度來看,克肖認為最常見的態度是對猶太人的遭遇漠不關心。[155]克肖稱大多數巴伐利亞人只是模糊地知道「浩劫」的存在,較之「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來說他們更關心正在進行的戰爭。[155]克肖做了一個類比:「仇恨建造了通往奧斯維辛的路,但做鋪墊的卻是冷漠。」[156][157]
克肖的觀點是巴伐利亞人就「浩劫」來說是冷漠的,並暗示德國大眾也同樣如此。這一觀點受到以色列歷史學家、納粹德國大眾意見專家奧托·德芙·卡爾卡(Otto Dov Kulka),和加拿大歷史學邁克·凱特(Michael Kater)的批評。凱特堅持克肖淡化了公眾的反猶情緒;納粹德國時期,許多「自發的」反猶行動上演,是由於許多德國人參與的緣故,但將納粹看成反猶主義的唯一源泉是錯誤的。[158]卡爾卡稱大多數德國人的反猶情結比克肖《第三帝國公眾意見和政治異議》中描寫的更加強烈,而不是簡簡單單的「冷漠」,「被動服從」可以說是在美化德國人了。[159]
在研究猶太或德意志反納粹統治問題上,德國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迪珀在他1983的論文《德國抵抗運動和猶太人》(Der Deutsche Widerstand und die Juden)稱絕大多數反納粹民族保守主義者也是反猶主義。[158]迪珀寫到民族保守主義「官僚就法律上對排斥猶太人一直到1938年都坐視不理。」[160]雖然迪珀注意到德國抵抗組織沒有一個支持大屠殺,但他也提到民族保守主義者也沒有打算在推翻希特拉後恢復猶太人的權益。[158]迪珀繼續辯稱,反對派「中大部分德國人... 認為「猶太問題」存在,應該得到解決...」。[158]
2012年的研究發現在柏林就有3,000個不同功能的集中營,在漢堡則有1,300個,研究員認為德國大眾不可能對這種大事兒不可能不知道。[10]羅伯特·蓋拉特萊認為德國民眾從總體上來講是知情的。蓋拉特萊稱,政府通過媒體公開了他們的計劃,民眾也都瞭然,只有毒氣室除外。[161]與之相反的是歷史證據顯示絕大多數受害人在送入集中營之前,不知道等待他們的命運是什麼,或是拒絕承認噩運;他們只是天真地認為自己不過是將被重新安置罷了。[162][163][164]

德國歷史學家漢斯·布海姆搜集了法蘭克福奧斯維辛審判的迫害見證人資料,在1965年寫成論文《命令與服從》(Command and Compliance)。文章提到屠殺猶太人和其他人時,命令並沒有添加脅迫,執行該命令的是出於自由意志。[165]布海姆寫道迴避執行殺戮命令的機會「...不但隨時出現,而且比人們所願意承認的更加實際...」[165],並寫道沒有證據顯示拒絕履行命令的黨衛隊員被拖入集中營或是被處決。[166]不但如此,黨衛隊規章禁止「無端的虐待」,希姆勒要求他的手下保持「風度」,虐待被認為是行為人極端殘忍,或是期望突出表現自己是個非常熱心的納粹黨員。[165]最後,他認為非犯罪傾向者施刑是因為他們願意遵守團體價值,害怕被貼上「懦弱」的標籤。[167]
大屠殺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寧於1992著書《普通人:預備警衛營101營和波蘭的最後解決方案》(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他在其中討論了德國秩序警察預備營101營,該營負責將猶太人圍捕,送往納粹死亡營。預備營的服役者都是來自漢堡的中年男子,工人階級出身。他們不適合執行軍事任務,也沒有在荼毒生靈上接受太多訓練。司令員則為部下給出選擇:如果他們覺得受不了的話,就可以不參加。絕大多數人沒有拒絕——一個500人的營中只有15人選擇退出。[168]根據米爾格拉姆實驗,布朗寧認為營隊的士兵們之所以殺人,是因為服從權威和朋輩壓力,而不是嗜血或是仇恨。該書的隱含意思是當環境是緊密團結的群體時,絕大多數人會服從權威,並被認為是合法的,雖然道德上感到令人憎惡——這一假說在米爾格拉姆實驗中得到了詳細研究。
俄國歷史學家賽奇·庫德里亞索夫(Sergei Kudryashov)對特拉維尼基黨衛隊集中營的守衛訓練做了研究,後者負責為萊因哈德行動死亡營提供協助。一些特拉維尼基的守衛是紅軍戰俘,他們自願參加黨衛隊以脫離戰俘營。[169]克里斯托弗·布朗寧在《普通人》(Ordinary Men)一書中寫道,檢驗那些與德軍合作者(一般通稱「志願者」)的方式為態度上是否反共(當然也就等同是否反猶)。[170]他們中絕大部分是烏克蘭、拉脫維亞、立陶宛的「志願協助者」,即非徳裔的德國軍人。[170]與布朗寧不同,庫德里亞索夫則稱他沒有發現特拉維尼基志願兵與反猶主義或納粹主義有絲毫的聯繫,[170]許多人在被俘虜前都是共產黨人。[171]雖然特拉維尼基守衛都沒有特殊情結,但他們依然執行了黨衛隊虐猶的命令,而他們在虐猶上是「系統性的、沒有理由的」。[171]雖然不是所有人都參加了行刑活動,但為萊因哈德行動死亡營服役的絕大多數人都殺了不少猶太人。[172]和布朗寧一樣,庫德亞斯紹夫辯稱特拉維尼基人是普通人變劊子手的典型案例。[173]
特拉維尼基人(Trawnikimänner)在所有主要滅絕營都有部署,負責協助「最終解決方案」——這也就是訓練他們的初衷。在那裏,他們都積極參與了迫害猶太人的活動。[170][174]
在1942年間,除了奧斯維辛營以外,其它五個地點也被設立為滅絕營,用以執行萊因哈德計劃。[185][186]其中兩個,即海烏姆諾營[187]和馬伊達內克營已經被用作苦役營,後被改裝、加入滅絕屠殺設備。三個新營被搭建了起來,單獨為快速屠殺使用,即貝爾賽克營、索比堡營、特雷布林卡營。第七個營是白俄羅斯的瑪麗·特羅斯特內茲營,也承擔同樣的任務。亞塞諾瓦茨營則負責解決塞爾維亞人。
滅絕營常常與集中營相混淆,如達豪集中營和貝爾森集中營。集中營主要在德國境內設立,負責關押囚徒、對納粹敵人施行苦役(如共產黨人或同性戀)。集中營也應該與苦役營區別開來,後者在所有德控區都有設立,負責對各種人士,包括戰俘在內,施行苦役。所有納粹營都遍佈飢餓、疾病、疲勞,因而死亡率極高,但滅絕營是單獨為大規模殺戮而設立的。
火車會開到一個叫做卸貨場的地方,車上滿載猶太人。他們被沒日沒夜地送過來,有時一天一次,有時一天五次…人們不停地從歐洲中心地區消失,他們來到同樣的地點,對之前人們的命運毫無知曉。大批大批的人們…我知道在幾個小時之內…他們中的90%都會被送入毒氣室。
滅絕營由黨衛隊管理,但絕大多數的守衛是烏克蘭、波羅的海輔助人員。普通德國士兵則被排除在外。
集中營毒氣室的人員都是由火車運送的。有時,火車直接開進毒氣室,但通常先由營地醫生對每個人進行篩檢,將一小部分適合工作的拉出來做苦役。絕大多數人則被送入接待區,在那裏脫光衣服、放下行李,交由納粹沒收,用以資助戰爭。之後,人們被赤身裸體地趕進毒氣室。通常情況下,他們得到的告知是浴室或是「除虱滅蚤室」,門外的告示是「洗浴」或「桑拿」。有時,守衛會給他們發放一小塊肥皂或毛巾,用以減輕恐慌,並提醒他們記住自己衣物存放的地方。坐車許久後人們喉嚨乾渴,提出要水喝時,被告知營地裏有咖啡等着,「趕快走,否則咖啡就涼了」。[188]

根據奧斯維辛營長魯道夫·霍斯的供述,第一室可容納800人,第二室可容納1,200人。[189]當屋子裝滿人後,門就被關上鎖死,齊克隆B從通氣孔被送入室內,釋放有毒的HCN,即氰化氫。室內的人會在20分鐘內死亡,死亡的速度則與囚徒離通氣孔的距離遠近有關。根據霍斯的觀點,1/3的受害人是立即斃命。[190]黨衛隊醫生約翰·克雷默(Johann Kremer)負責監視毒氣釋放,他作證稱:「受害人的呼喊和尖叫可以從開口處聽見,很明顯,他們在為性命掙扎。」[191]由於毒氣室常常人滿為患,當開門處理時,受害人的姿勢常常是半蹲着的,他們皮膚的顏色為粉色,有紅色和綠色的斑點,有的嘴上口吐白沫,有的耳朵出血。[190]
之後,毒氣被排出,屍體被移除(可能會用上4個小時),黃金假牙或蛀牙上的鑲金會由懂得牙醫學的囚徒用鉗子剝離,婦女的頭髮會被剪除。[192]毒氣室的地面被清理,牆壁被粉刷。[191]這項工作由特遣隊負責,隊員則為猶太囚徒。在第1、2號火葬場,特遣隊員住在火葬場上方的閣樓裏;在第3、4號火葬場,他們住在毒氣室中。[193]當特遣隊員處理完屍體後,黨衛隊士兵對其進行抽查,確認所有的黃金都從受害人的嘴裏剝離出去。如果發現有遺漏的,那麼對其負責的特遣隊員會被扔進火爐,以示懲罰。[194]
最初,屍體被放入深坑,蓋上石灰。在1942年9-11月,希姆萊下令,屍體被掘出焚燒。在1943年早期,新的毒氣室和火葬場被建造,以適應眾多的人數。[195]
在特雷布林卡,我們所做的一大改進就是建成一次能容納2,000人的毒氣室,而之前的10個毒氣室一次只能容納200人。我們篩選人員的方式如下:奧斯維辛的兩個黨衛隊醫生負責檢查到來的囚徒。囚徒在醫生面前走過。能幹苦工的就留在營中,其它的就被立即送往滅絕營。兒童和未成年人格殺勿論,因為他們無法勞動。在特雷布林卡,我們所做的改進是囚徒知曉自己的命運,而在奧斯維辛,我們努力地告訴他們這不過是個滅虱的過程罷了。當然,他們很快就知道我們的意圖,便常常暴亂,惹出麻煩。婦女常常將孩子藏在衣服裏,當然,一旦被發現,我們就把孩子解決掉。根據要求,我們必須將這些工作秘密進行,但是焚燒屍體所產生的噁心臭氣瀰漫在整個地區,所有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奧斯維辛在殺人。
——魯道夫·霍斯,奧斯維辛營長,紐倫堡證詞。[196]
总结
视角


在《歐洲猶太種族的毀滅》[197]一文中,勞爾·希爾伯格寫到:
猶太人對此所做的反應的典型特徵是幾乎完全沒有任何抵抗。與德國納粹的宣傳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對猶太人的反抗進行記錄的歷史文獻,無論是毫不隱晦的直接描述還是委婉的間接記錄都少之又少。在整個歐洲範圍內,猶太民族並沒有建立任何反抗組織,也沒有任何武裝行動計劃和藍圖,甚至連心理戰的計劃方案都沒有。這些猶太人完全是毫無準備、措手不及的。
… 按照德國納粹對傷亡人數的統計,猶太人的武裝反抗被弱化到微不足道的水準。
… 整個毀滅過程的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取決於猶太人的參與度,從個人零散的單獨的行為到群體的有組織的統一行動。
… 一些猶太人的反抗組織試圖扭轉大屠殺開始時整個猶太民族的無抵抗狀態,這些反抗組織喊出了「不要做等待宰殺的羔羊」的口號。
… 一次在德國西部的一個監獄中,有人問掌握着兩個死亡集中營的佛朗茲·斯坦格爾(Franz Stangl),他對猶太難民所做的回應是什麼。佛朗茲·斯坦格爾說,直到最近他才讀到了一本關於旅鼠的書,這本書讓他想起了特雷布林卡。[198]
彼得·隆格里奇(Longerich)在他所做的一項重要研究中發表了類似的看法:「從猶太人的角度來看,他們幾乎沒有做任何抵抗」。[199]希爾伯格提到了猶太人歷史上所遭受的迫害,以此來解釋猶太人對這次大屠殺所表現出的服從態度:過去的幾個世紀以來,猶太人在遭受迫害時一貫的做法就是向壓迫者發出籲求,服從命令,以期能夠避免使矛盾進一步激化,從而減輕猶太人所受到的傷害,一直忍耐,直到大屠殺結束。「在這些遭受壓迫的歲月裏,太多的猶太人成為犧牲品。但是猶太民族總是能夠重新站起來,就像一塊岩石從退去的浪潮中再次嶄露頭角。猶太民族從未從地球上消失過。」他們只是「被歷史的夾縫困住」,而且等他們意識到這是一個艱難的時期時,已經是很久以後的事情了。[200]
提摩希·D·史奈德在討論華沙猶太區起義這一事件時也表達了相似的看法,他指出,大規模驅逐發生之後,僅僅是在1942年7月到9月這三個月期間,猶太民族才達成一致意見,共同意識到武裝抵抗的必要性。發源於猶太保守政治中心的被動性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猶太人群體與戰前的波蘭政府達成讓步協議從而取得了整體勝利。[201]到最大規模的武裝反抗運動爆發時,也就是1943年爆發的華沙猶太區起義,只有少數波蘭猶太人倖存。[199]
耶胡達·鮑爾以及其他歷史學家爭論說,猶太人的反抗運動不僅包括身體反抗,也包括任何使猶太人在充滿屈辱和慘無人道的條件下重獲尊嚴和人權的精神反抗活動。[202]
在每個猶太人聚居區,在每次大驅逐過程中,在每個勞工營地、甚至在死亡集中營中,反抗的意願是強烈的,且以多種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以所能夠找到的為數不多的武器進行抗爭,個人的反抗和抗議行為,在死亡的威脅之下尋找食物和水的勇氣,讓德國人無法實現其對猶太人的驚慌和絕望幸災樂禍的無恥企圖。
甚至於無抵抗也是一種抵抗形式。死的有尊嚴也是一種抵抗形式。抵抗殘酷的讓人絕望的邪惡力量、拒絕讓自己被降低到和動物同等的水準、經受痛苦和折磨的考驗、讓摧殘者比自己更早地進入墳墓,這些都是猶太人的抵抗行為。最後,僅僅是見證這些事件就是對最終的勝利所做的貢獻。讓自己存活下來就是人類精神的勝利。
——馬丁·吉爾伯特。《大屠殺:猶太人的悲劇》[203]

希爾伯格爭辯說,不能高估猶太人的反抗力度,也不能採用吉爾伯特對猶太人的反抗活動所做的無所不包的定義。「當相對孤立的或分散性的抵抗行為代表着典型的猶太人反抗行為,則德國人的衡量尺度的一個基本特性就被湮沒了」,也就是說,對溫順無辜的人民所做的慘無人道的屠殺被美化成某種形式的戰爭。「反抗活動的高漲帶來的另一個後果是,自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反抗者的猶太人對這一現象感到憂慮。如果英雄氣概屬於歐洲猶太群體中的每一個成員,則真正採取行動的少數猶太人的功績就會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最後,採取被動態度的大多數猶太人和採取積極行動的少數猶太人被混合在了一起,「這不僅是一種稀釋形式,在一個謹慎而不願抵抗的民族中組織抵抗運動會面臨多種多樣的問題,而這種混淆就遮蓋了這些問題;這種混淆也迴避了許多與這一群體相關的問題,包括該群體的思維方式以及生存策略。」如果不提及這些問題,就沒有辦法書寫猶太人的歷史。[204]
最著名的猶太人武裝反抗活動就是爆發於1943年1月的華沙猶太區起義,在這次起義過程中,武器裝備非常簡陋的幾千名猶太戰士迫使SS陷入困境並持續四周的時間,但是隨後這些猶太武裝力量被遠遠強大於其的武裝力量擊潰摧毀。根據猶太人的敍述,在這次起義過程中,有幾百名德國士兵被殺,而德國人卻對外聲稱只有17名士兵被殺害,93名士兵受傷。根據德國納粹的統計數字,有13000名猶太人被殺,57885名猶太人被驅逐。這次起義結束之後,緊接着,1943年五月,位於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營的猶太人爆發了反叛運動,其中200名猶太人從集中營中逃出。他們制服並殺死了一些德國納粹護衛,並放火燒了集中營,但是在這次反叛過程中,有900名猶太人被殺害,在600名成功出逃的猶太人中,只有40人在戰爭中倖存下來。兩周之後,在比亞韋斯托克猶太區也爆發了起義運動。
九月份,在維爾納猶太區爆發了一場短暫的起義。十月份,600名猶太囚犯,包括猶太蘇聯戰俘,試圖逃離索比堡死亡集中營。猶太囚犯殺死了11名德國納粹黨衛隊長官以及一些集中營護衛。但是,這一行為被德國納粹軍隊發現了,納粹軍隊企圖放火燒死這些猶太囚犯,結果集中營中的猶太人不得不在熊熊烈火中奔忙逃命。在這次逃亡過程中,犧牲了300名猶太囚犯。而那些倖存者要麼在營地周圍的礦場中喪生,要麼重新被俘虜並慘遭殺害。大約只有60名猶太人成功逃離了集中營並加入了蘇維埃黨派。1944年10月7日,位於奧斯維辛的250名猶太特遣隊隊員攻擊了守衛,並用炸藥炸了四號火葬場,這些炸藥是三名女囚犯從附近的一個工廠中偷偷運出來的。在這次起義過程中,有三名德國納粹守衛被殺死,其中一個被塞到了火爐中。特遣隊隊員試圖發起一場大規模的起義運動,但是很快全部250名猶太特遣隊隊員都被殺害了。
據估計,在東歐,大約有20,000到30,000名猶太游擊隊員積極地同納粹分子及其勾結者作戰。[205][206]這些游擊隊員致力於與納粹分子展開游擊戰和破壞活動,鼓動居住於猶太區的猶太人起義,並釋放猶太囚犯。僅僅在立陶宛,這些猶太游擊隊員就消滅了將近3000個德國士兵。參加同盟軍軍隊的猶太士兵多達140萬人。[207]其中,大約40%的猶太士兵在蘇聯紅軍軍隊中作戰。[207]在參加蘇聯紅軍隊伍的猶太士兵中,大約200,000名猶太士兵在戰爭中犧牲。[208]在英國軍隊中,有一個猶太人組成的軍隊積極同納粹分子作戰,這個猶太軍隊是由5000名來自英屬巴勒斯坦託管地的志願者所組成的。在西部沙漠戰役中,來自於特殊聞訊小組的以德語為主要語言的猶太志願者組成了突擊隊,在前線後方對納粹黨實施破壞活動。
在被納粹佔領的波蘭和蘇維埃領地上,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成批逃離到沼澤地或森林中,或加入了游擊隊,儘管游擊隊組織並非總是歡迎這些猶太難民的加入。在立陶宛和白俄羅斯,有一個區域聚集着眾多的猶太人,且這一區域也是非常適合游擊作戰的區域,在這裏,猶太游擊隊拯救了成千上萬的猶太難民,使其免遭屠殺的厄運。而對於生活於布達佩斯等城市裏的猶太群體而言,就沒有這樣好的機遇了。但是,在阿姆斯特丹以及荷蘭的其他地方,許多猶太人積極地活躍於荷蘭反抗運動中。[209]蒂莫西·斯奈德寫到,「華沙起義運動中的其他戰士是1943年猶太區起義遺留下來的老兵。在這些猶太人中,大多數猶太人都加入到了波蘭家鄉軍中;其他一些猶太人加入到了人民軍隊中,或者甚至加入到了反猶主義的國家武裝軍隊中。一些猶太人(或是猶太族裔的波蘭人)已經加入了家鄉軍軍隊和人民軍隊。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參與了1944年8月的華沙起義運動並作戰的猶太人的人數超過了1943年4月的華沙猶太區起義運動中的猶太人的人數。」[210]參加游擊隊僅僅是年輕健壯且願意離開家人的猶太人的一種選擇。許多猶太家庭更願意死在一起而非被分離。
法國猶太人也非常積極地參加了法國抵抗運動,法國的抵抗運動對納粹和法國維希當權者進行了游擊作戰,並且為橫掃法國的同盟軍提供了幫助,為同盟軍提供了支持,包括解放法國的武裝力量,和同盟軍一起為解放許多被佔領的法國城市而作戰。儘管猶太人在整個法國人口中僅僅佔到百分之一的比例,但是在法國反抗運動中,猶太人的人數佔到整個反抗隊伍的15%到20%。[211]猶太青年運動EEIF最開始時對維希政權表示了支持的態度,但是到1943年這項運動被當局禁止,這一組織中的許多成員又組成了武裝反抗團隊。猶太復國主義者也組建了猶太軍隊(猶太人的軍隊),這些軍隊在猶太復國主義的旗幟下參與了武裝反抗活動,並幫助猶太人秘密地逃離法國。這兩個組織在1944年合併為一體,並參加了解放巴黎、里昂、圖盧茲、格勒諾布爾和尼斯的戰鬥。[212]
許多人認為大屠殺中的猶太人就像等待宰殺的羔羊,沒有任何的反抗,但是這並非真實的情況——可以說這是完全錯誤的看法。在反抗運動中,我與許多猶太人並肩作戰,密切協作,我可以告訴你們,他們敢於承擔的風險遠遠超過我所願意承擔的風險。
——皮特·米爾伯格(Pieter Meerburg)[213]

對於絕大多數的猶太人而言,反抗運動只能採取延遲、逃避、協商、談判等被動的形式,在可能的情況下,還可以採取賄賂德國官員的形式。納粹分子強迫猶太人群體自行維持群體的治安,通過在德國建立德意志猶太人協會(Reichsvereinigung der Juden)和在被佔領的波蘭領地的城市猶太區中組建「猶太居民委員會」等組織,以此誘使猶太人採取賄賂德國官員的形式來逃避迫害。每當猶太人拿出賄賂用的財物時,德國軍官就承諾做出讓步,這使得猶太群體中的領導者在這種善意的妥協行為中越陷越深,使得猶太群體不可能做出奮起反抗的決定。猶太人大屠殺中的倖存者亞歷山大·基梅爾(Kimel)寫道:「居住於猶太區的青年人幻想與納粹分子作戰,我認為儘管存在着多種因素阻礙我們對此做出回應,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是隔離和歷史上形成的接受殉難的心理。」[214]
歷史條件使得生活於歐洲的猶太群體形成了接受迫害和通過妥協和談判來避免災難的心理趨向,這是大屠殺過程中猶太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未能做出反抗決定的最重要的因素,直到大屠殺接近尾聲時,猶太人才做出了反抗行為。直到當猶太人口從500,000人銳減到100,000人時,華沙猶太區起義運動才興起,直到這時,猶太人才明白進一步的妥協已經是不可能的了。保羅·約翰遜寫道:
猶太人遭受迫害的歷史長達一千五百年之久,在這場曠日持久的遭受迫害的歷程中,猶太人形成的一種觀點是,反抗只會帶來犧牲,而不能自我拯救。猶太人的歷史、猶太人的神學理論、猶太人的民間風俗、猶太群體的社會結構、甚至猶太人的語言詞彙都造就了猶太人甘願協商、甘願付出、甘願懇求、甘願抗議,而不願戰鬥的特點。[215]
對於德國納粹的真正意圖,猶太人群體一直被蒙在鼓裏,可以說這種欺騙是系統性的,猶太人與外部世界的新聞來源之間被隔絕。德國納粹黨告訴猶太人他們要被轉移到工作營地——委婉地稱之為「移居到東部」——並通過各種縝密的謊言來維持這一假象,直到猶太人到達毒氣室的門前(因為毒氣室的門上張貼有標識,指明這是用於消滅虱子的毒氣室),德國納粹黨的欺騙和謊言都是為了避免猶太人的反抗。從照片中可以看出,猶太人在奧斯維辛和其他死亡集中營所在地的火車站下車,提着麻袋和手提箱,從他們的神態可以看出他們對等待着他們的厄運一無所知。關於死亡集中營的真相的傳言通過層層阻礙傳播到猶太區已經是很晚以後的事情了,且通常這些傳言並未被猶太區的居民採信,正如當波蘭反抗戰鬥的戰士兼情報員簡·卡斯基(Jan Karski)把消息帶到西方同盟國時,這些消息並未得到同盟國的信任。[216]
总结
视角

1942年6月萊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布拉格被暗殺。接替他擔任黨衛隊國家安全部職位的是恩斯特·卡爾滕布倫納。卡爾滕布倫納和艾希曼在希萊姆的密切掌控下,監視着「最終解決方案」進行到高潮階段。從1943年到1944年,死亡集中營屠殺猶太人的速度幾近瘋狂,這些猶太人被火車從德國勢力範圍內的各個國家運往此處,等待被屠殺。到1944年的春天,每天在奧斯維辛有8000人被毒氣殺害。[217]
儘管以猶太人聚居區為基地的軍事工業的生產量非常高,但是1943年這些軍工工廠卻被清算關閉,而軍工廠的工人也被送往集中營等待屠殺。其中最大規模的一次轉移是1943年初期華沙猶太區的100,000名猶太人被送往集中營,這一事件成為了華沙猶太區起義的導火索,而這一起義也遭到了殘酷鎮壓。1943年11月3日至4日,在收繳行動中(Aktion Erntefest),大約42000名猶太人被射殺。[218]與此同時,列車每天從歐洲西部和歐洲南部出發,定時達到集中營所在地。居住於被佔領的蘇維埃領地的猶太人很少有被轉移到集中營的:這一地區的猶太人的殺戮工作被轉交給了黨衛隊負責,並由從當地收錄的附屬軍隊提供協助。無論是採用了哪種屠殺方式,到1943年,活動於大多數蘇維埃領地的德國人都被驅逐了出去。

德國鐵路的主要運輸對象就是猶太人,猶太人被成批地運往集中營,1942年年底史太林格勒戰役結束之後,德軍面臨的軍事局面更為殘酷,且同盟國加緊了對德國工業和運輸業的空襲,即使在這個時候,德國的鐵路和列車仍然源源不斷地把各地的猶太人送往集中營。軍隊的首領和經濟領域的管理者抱怨其人力資源被截流,且造成了大批難以被取代的熟練的猶太技術工人被殺害。但是到了1944年,很明顯,大多數德國人不再被納粹黨的狂熱盲從所迷惑而失去理智,且德國在這場戰爭中必將失敗已經稱為一個明了的事實。許多高級軍官開始害怕等待着德國的報應和後果,更是懼怕他們作為個人將要遭到的報應,因為他們犯下了如此多的罪行,太多的罪孽都是以他們的名義而付諸實施的。但是希姆萊的軍隊和德意志帝國的黨衛隊太過強大,難以反抗,且希姆萊總是能夠使希特拉的政權聽從於他的命令。
1943年10月,希姆萊向駐紮波森(現波蘭波茲南)的納粹黨的高級官員發表了講話。在這次講話中,希姆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直白地表明了他的真實意圖,他致力於滅絕歐洲的猶太種族:
在這裏,我的周圍都是同我的關係最為密切的官員,我們納粹黨的同志,我要向你們提到一個問題,一個所有人都認為理所當然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對我而言卻是一生中最困難的問題,那就是猶太人的問題……我向你們提出一個要求,那就是我在此所講的每一句話你們都只能認真地傾聽,但是絕對不能對外人提到一個字……我們所要談論的問題是:這些婦女和兒童應當如何處理?對此我已經想出了一個非常清晰的解決方案。我並不認為我命令滅絕這些男人是有充分理由的——也就是說殺掉他們或命令士兵殺掉他們——並讓僅僅是兒童的復仇者長大成人……我們必須要做這個最艱難的決定,讓這個民族從地球上消失。

這場講話的聽眾包括海軍上將卡爾·鄧尼茨和軍備部長阿爾伯特·斯佩爾。在紐倫堡審判中,鄧尼茨聲明他對「最終的解決方案」一無所知,並且得到了法庭的採信。但是,斯佩爾在紐倫堡大審判中以及隨後的一場採訪中聲明「如果我沒有看,那是因為我不想去看」。[219]在對這兩個人進行審判時,這篇談話尚未得到披露。
1944年初,大屠殺的規模有所縮減,因為被佔領的波蘭境內的猶太人聚居區已經被清空了,但到了1944年3月19日,希特拉命令對匈牙利進行軍事佔領(瑪格麗特行動),且艾希曼被派遣到布達佩斯,監督匈牙利800,000名猶太人被驅逐出境。在此之前的一天,也就是1944年5月18日,希特拉曾私下裏向匈牙利攝政王兼海軍上將霍爾蒂·米克洛什抱怨說:
匈牙利在猶太人的問題上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也沒有準備好與生活於此的猶太群體進行清算。[220]
在這一年中,超過一半的猶太人都被運往奧斯維辛。在接受審判時,指揮官魯道夫·霍斯說在三個月的時間裏他殺害了400,000名匈牙利猶太人。
屠殺匈牙利猶太人的計劃在納粹內部遭到了反對,一些人建議希特拉應與盟國進行交易,釋放這些猶太人以換取有利的和平協議。在伊斯坦布爾,希姆萊的代理人與英國特工及猶太組織的代表曾進行過非正式的商談,艾希曼曾一時計劃以一百萬猶太人交換一萬卡車的貨物——即所謂「鮮血換貨物」計劃,但這樣大規模的交易並沒有實際可能。

從集中營逃出來的猶太人是非常少的,但是這些人並非是不為人知的。1944年,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指揮官報告說「當地的居民是狂熱盲信的波蘭人,且……隨時準備對他們無比憎恨的黨衛隊集中營工作人員採取任何行動。每一個設法成功逃離集中營的囚犯一經到達他們所遇到的第一個波蘭農莊,就會立刻得到這些狂熱的波蘭人的幫助。」[221]但是,根據路德·林(Ruth Linn)的描述,從集中營中逃離出來的囚犯,尤其是猶太囚犯,根本不能指望當地居民或波蘭的地下組織為其提供幫助。[222]
1942年2月,一名從切姆諾死亡營逃出來的囚犯,雅各·雅諾維斯基(Grojanowski),抵達了華沙猶太區,他向華沙猶太區一個安息日群體(Oneg Shabbat)詳細地講述了切姆諾集中營的情況。他的報告被稱為雅諾維斯基報告,通過波蘭的地下組織(Delegatura Sił Zbrojnych na Kraj)將這些消息傳播到了猶太區以外的波蘭烏茲市,到1942年6月,這些消息傳播到了倫敦。到這時為止這些人聽到該報告之後採取了什麼行動是不得而知的。[179][223][224][225] 與此同時,到2月1日美國的軍事信息辦公室決定不對外公佈關於集中營對猶太人的屠殺情況的信息,因為這會誤導民眾誤認為這場戰爭僅僅是一個關於猶太人的問題。[226]
直到1942年10月9日,英國的無線電台才將猶太人被送往毒氣室殺害的新聞傳播到了荷蘭。[227]1942年12月,西方同盟國發表了由聯合國成員國共同簽署的聯合聲明。這份聯合聲明描述了「希特拉一再表露出來的屠殺和滅絕歐洲的猶太民族的意圖」是如何得到貫徹執行的,並宣佈同盟國「以最強烈的言辭譴責這一冷血屠殺的野蠻政策。」[228]
1942年,卡斯基向波蘭政府、英國政府和美國政府匯報了波蘭的情況,尤其是華沙猶太人聚居區被毀的情況,以及猶太人遭遇大屠殺的情況。卡斯基與被放逐的波蘭政治家會面,包括波蘭總理以及社會黨、國家黨、勞工黨、人民黨、猶太人同盟、錫安工人黨等政黨的成員。他還同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進行了交談,並向安東尼·艾登詳細講述了他在華沙和貝爾賽克的所見所聞。[229]1943年,卡斯基在倫敦會見了當時非常有名的記者阿瑟·庫斯勒。隨後卡斯基前往美國,並向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做了匯報。卡斯基的報告對於讓西方同盟國了解歐洲猶太人的情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3年7月,卡斯基再次私下向羅斯福總統匯報了波蘭的情況。卡斯基還與美國許多其他政府領導和民間團體的領導會面,其中包括費利克斯·弗蘭克福特、科德爾·赫爾、威廉·約瑟夫·多諾萬以及斯蒂芬·塞繆爾·懷斯。卡斯基還把他的報告通知了媒體、各種不同教派的主教(包括紅衣主教塞繆爾·斯特里奇)以及荷里活電影產業的相關人員和藝術家,但是卻沒有取得成功。他的許多聽眾並不相信他所講述的內容,或者認為他的描述過於誇張,或者認為他只是在為波蘭流亡政府做宣傳。[230]
關於猶太人被趕進毒氣室中然後被殺害的新聞還在荷蘭反抗組織舉辦的一些非法報紙上出版了,如1943年9月27日《荷蘭國家日報》(Het Parool)上刊登的一篇新聞。但是,這些新聞讓人感到太過不可思議,以至於許多人認為這僅僅是在為戰爭做宣傳。由於這些新聞對荷蘭的反抗活動起到了反作用,因此這些新聞的出版被迫停止了。然而,許多猶太人卻因此而得到了警告,這些刊物警告猶太人他們面臨着被謀殺的危險,但是對於大多數猶太人而言,逃離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寧願相信這些警告都是虛假的。[231][232]
1940年9月,作為波蘭地下黨、家鄉軍的一名成員,維托爾德·皮爾基上校想出了一個進入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方案,那就是主動要求被送往奧斯維辛,他是唯一一個主動要求被送往奧斯維辛並被囚禁的人。他組織了一個地下網絡——軍事組織聯盟(Związek Organizacji Wojskowej),這個地下網絡可隨時發起一場起義運動,但是該組織認為起義成功的概率非常低。軍事組織聯盟所提供的許多詳細的報告成為西方同盟國獲取關於奧斯維辛集中營情報信息的主要來源。1943年8月,皮爾基從奧斯維辛集中營逃出來,並帶來了重要信息,這些信息成為一份包含兩部分的報告的基本依據,這份報告後來被送到了位於倫敦的戰略情報局(OSS)。該報告中包含了關於毒氣室的詳細信息,也講述了「挑選」過程以及消毒試驗。報告中陳述說,比爾克瑙有三個火葬場,每天能夠焚燒10000個人,且一天之中有30000人都被毒氣殺害。作者寫道:「在歷史中再也無法找到如此殘忍地殘害人類生命的先例」。[233]戰爭結束之後當皮爾基返回波蘭時,共產黨當局逮捕了他,指控他為波蘭流亡政府間諜。在一場擺樣子的審判中他被處以死刑,並在1948年5月25日被處決。
皮爾基從奧斯維辛逃出來之前,1942年6月20日發生了最大規模的逃亡事件,當時,烏克蘭人歐根紐什·本德拉(Eugeniusz Bendera)以及三名波蘭人——卡齊米日·佩特羅夫斯基、斯坦尼斯·亞斯特爾(Stanisław Gustaw Jaster)和約瑟夫·蘭帕特(Józef Lempart)——勇敢地做出了逃亡的舉動。[234]這些逃亡者穿着黨衛隊士兵的服裝,全副武裝,並開了一輛黨衛隊用車。他們開着一輛偷來的斯泰爾牌(Steyr)220型號的汽車駛出了主大門,並帶着皮爾基為波蘭反抗組織所寫的關於大屠殺的第一份報告。德軍未能抓到他們中的任何一個。[235]
1944年4月,猶太囚犯魯道夫·弗爾巴和阿爾弗雷德·韋茨勒從奧斯維辛集中營逃出,最終抵達了斯洛伐克。他們提交給猶太官員的一份長達32頁的文件中講述了奧斯維辛集中營中大規模屠殺的情況,這份報告後來被稱為《弗爾巴—韋茨勒報告》。弗爾巴對那段時期有着異常清晰的記憶,他在猶太人站台工作,猶太人在這裏下車之後,或者被挑選送往毒氣室,或者被選出來作為奴隸工人。他對這裏的情形所做的描述的詳細程度使得斯洛伐克的官員能夠將他的敍述與這些官員自己的驅逐出境的記錄進行比較,且如此確切的敍述讓同盟國相信了這份報告的內容,並且認真地對待這份報告。[236]
1944年5月27日,另外兩名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囚犯——阿爾諾斯特·羅森(Arnost Rosin)和切斯拉夫·米沃什(Czesław Mordowicz)從集中營中逃出,並於6月6日抵達了斯洛伐克,這一天是諾曼第登陸的日子(D日)。聽聞諾曼第登陸的消息,他們以為戰爭結束了,並大醉了一場來慶祝戰爭的勝利,買酒的錢是他們從集中營中偷偷帶出來的。由於觸犯了當時的貨幣法律,他們被逮捕了,並在監獄中度過了八天,直到猶太居民委員會為他們交了罰款。他們為猶太居民委員會所提供的額外信息也被添加到了「弗爾巴—韋茨勒報告」中,且這些信息後來被稱為「奧斯維辛方案」。他們報告說,1944年5月15日到5月27日,有100,000名匈牙利猶太人抵達了比爾克瑙,並被迅速殺害,他們被殺害的速度是史無前例的,而屍體上的脂肪則用來加速焚燒。[237]
1944年6月15日[238]、6月20日、7月3日[239]和7月6日[240],BBC和《紐約時報》刊載了弗爾巴—韋茨勒報告中所提供的材料。接下來,1944年7月9日,來自世界各國領袖的壓力迫使霍爾蒂·米克洛什停止了大規模地把匈牙利的猶太人轉移到奧斯維辛,因此挽救了200,000名猶太人的性命,使其免遭屠殺。[237]
2011年11月14日,在150周年紀念日那一天,《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由前任編輯馬克思·弗蘭克爾(Max Frankel)撰寫的文章,這篇文章寫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以及戰爭期間,《紐約時報》對於報道什麼樣的新聞、登載什麼樣的社論是有嚴格的政策約束的,這些政策將關於大屠殺的報道減少到最低限度。[241]《紐約時報》認可了新聞學教授羅雷爾·萊夫(Laurel Leff)所做的詳盡的分析和所得出的研究發現,之前那一年裏,羅雷爾·萊夫教授在《哈佛國際新聞和政治期刊》中發表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指出,《紐約時報》故意迴避關於第三帝國迫害和謀殺猶太人的新聞報道。[242]萊夫得出的結論是,《紐約時報》的新聞報道和社論刊登政策使得生活於美國的猶太人幾乎不可能讓國會、教會或政府領導人意識到為歐洲猶太人提供幫助的重要性。[243]
总结
视角

到1944年中期,「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已經幾乎得到了徹底的實施。納粹黨政權可以輕易掌控的那些猶太人群體幾乎被全部滅絕,其中法國猶太人被殺害的人數所佔比例達到25%,而波蘭的猶太人被殺害的人數所佔比例達到了90%。1944年5月5日,希姆萊在一次講話中聲稱「在德國以及德國佔領的國家中,猶太人的問題整體上得到了解決。」[244]1944這一年間,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一任務都變得愈發困難。德國軍隊被驅逐出了蘇聯,巴爾幹半島各國的軍隊、意大利的軍隊以及德國的軍隊——包括與其結盟的國家最終結果不是戰敗,就是加入同盟國陣營。六月份,西方同盟國在法國登陸。同盟國對法西斯國家的連番空襲以及游擊戰爭使得鐵路運輸越發困難,且軍隊方面對德國將鐵路運輸線路用於向波蘭轉移猶太人的做法所表示的強烈反對越發迫切,已經不能繼續忽視。
這時,由於蘇聯紅軍逐漸逼近,位於波蘭東部的集中營被關閉,所有倖存的囚犯都被送往距離德國更近的西部集中營,首先送到奧斯維辛,隨後又送到西里西亞的羅森(Gross Rosen)。當蘇聯軍隊到達波蘭時,奧斯維辛集中營也被關閉了。最後的十三名囚犯全部是婦女,這些囚犯於1944年11月25日在奧斯維辛II號集中營被殺害;記錄顯示,這些囚犯「全部被殺害」(unmittelbar getötet),而至於他們是被毒氣殺害的或是以其他方式殺害的,則沒有相關記錄。[245]
儘管德國法西斯軍隊的戰事狀況已經瀕於絕境,但是納粹分子仍然盡極大的努力掩蓋集中營所發生的事實,並隱藏證據。毒氣室被拆毀,火葬場被炸毀,亂葬崗被挖開,屍體被焚化,納粹分子甚至哄騙波蘭的農民集中營舊址上種植莊稼,造成一種這些屠殺現場從未存在過的假象。當地的指揮官繼續屠殺猶太人,並強迫猶太人登上「死亡之旅」,在各個不同的集中營地之間來回輾轉,直到戰爭結束前的最後幾周。[246]
經過數月或數年的暴力迫害和飢餓的折磨,這些囚犯已經身患疾病,但是納粹分子還強迫這些囚犯登上長途跋涉的旅程,在大雪中一步步地走到火車站,然後在火車上經受幾天的旅途,在這一過程中,沒有食物也沒有遮風擋雨的物體,這些囚犯擠在貨運列車露天的車廂中,然後達到新的目的地之後,這些囚犯又被迫跋涉很遠的距離直到到達新的集中營。落在隊伍後面的或摔倒的囚犯都被立刻射殺了。在這些長途跋涉的過程中,大約250,000名猶太人在途中喪生。[247]
規模最大且最為人熟知的一次死亡之旅發生於1945年1月,當時蘇聯紅軍正向波蘭進駐。在紅軍到達奧斯維辛九天之前,黨衛隊驅趕着60,000名囚犯離開集中營,朝向沃濟斯瓦夫的方向行進,沃濟斯瓦夫與奧斯維辛相距56公里,這些囚犯被塞進貨運列車的車廂裏運往其他集中營。大約15,000名囚犯在途中死亡。埃利·維瑟爾和他的父親什羅莫(Shlomo)也是行進隊伍中的成員:
刺骨的寒風猛烈地吹着。但是我們卻一路走着,不能顫抖……
夜晚漆黑一片。夜空中時不時地出現爆炸的光亮。他們得到的命令是,任何趕不上隊伍的囚犯都要立即射殺。他們的指頭就放在扳機上,他們非常享受這種樂趣。如果我們中的某個人停下一秒鐘,一聲尖利的射擊聲就立刻了結了又一個「污穢的狗崽子」。
在我的附近,不斷地有人倒在骯髒的雪地裏。槍聲不斷。[248]

1944年7月23日,進軍途中的蘇軍發現了第一個大型集中營,馬伊達內克集中營。1945年1月20日,蘇軍解放了切姆諾集中營。1945年1月27日,蘇軍解放了奧斯維辛集中營;[249]4月11日,美軍解放了布痕瓦爾德集中營;[250]4月15日,英軍解放了伯根-貝爾森集中營;[251]4月29日,美軍解放了達豪集中營;[252]同一天,蘇軍解放了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5月5日,美軍解放了毛特豪森集中營;[253]5月8日,蘇軍解放了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254]而特雷布林卡、索比堡和貝爾賽克集中營卻沒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1943年納粹就已經焚毀了這幾個集中營。美國第七陸軍的上校威廉姆·W·奎恩談到了達豪集中營:「在那裏,我們的軍隊所見到的場景、所聽到的聲音、所聞到的惡臭,都是我們難以想像的,這裏所上演的慘無人道之劇烈,已經到了正常人無法理解的程度。」[255][256]

在蘇聯軍隊所發現的大多數集中營中,幾乎所有的囚犯都已經被消滅,只剩下幾千個倖存的囚犯——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找到了7,600名囚犯,[257]其中包括180個兒童,這些兒童成為了納粹醫生手下的試驗品。在卑爾根—貝爾森集中營,英國第11裝甲軍發現了60,000名囚犯,[258]還有13,000具尚未掩埋的屍體,還有10,000人在接下來的幾周內因斑疹傷寒或營養不良而死。[259]英軍勒令剩餘的黨衛隊守衛將所有的屍體聚集到一起,並將這些屍體葬入亂葬崗中。[260]
BBC的記者理查德·丁布爾比講述了他以及英軍在貝爾森所見到的場景:
這裏,在面積超過一公頃的土地上躺着無數的屍體和垂死的人。你無法分辨所見到的人或物體……掙扎着尚未死去的人們頭枕着屍體,周圍是那些可怖的鬼一樣的人群,他們瘦骨嶙峋,漫無目的地移動着,不知道該做些什麼,也不知道還能對生活抱有什麼希望,他們挪不動步子,無法承受周圍駭人的場景……這裏也有嬰兒出生,這些嬰兒小的可憐,非常衰弱,難以存活……一位被這個地方逼瘋的母親對着英國哨兵聲嘶力竭地尖叫,要給孩子餵奶,她把那小的可憐的小孩抱在懷裏……那名哨兵打開了嬰兒的襁褓,發現那個嬰兒已經死去多日了。這一天,在貝爾森所見到的一切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所見過的最可怕的場景。[261]
受害人與死亡人數
受害者人數的統計因「大屠殺」(Holocaust)一詞的定義而不同。[275]唐納德·涅維克(Donald Niewyk)和弗朗西斯·尼科西亞(Francis Nicosia)認為該詞指代是針對五百萬歐洲猶太人大屠殺行為,他們亦稱 Holocaust 一詞「沒有一個能令所有人滿意的定義」。[276]根據馬丁·吉爾伯特(Martin Gilbert)的估計,總的遇害者人數在六百萬以下,約佔當時730萬歐洲猶太人的78%。[277]蒂莫西·D·斯奈德寫道:「Holocaust 一詞的使用情況可分兩種:指代德國在戰爭中的所有屠殺行徑,或是指所有納粹政權對猶太人的壓迫行為。」[278]
廣義上,西方語境中的「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的受害者包括約200到300萬蘇聯戰俘、200萬波蘭人、150萬羅姆人、20萬殘疾人、政治或宗教異見者、15,000名同性戀及5000名耶和華見證人,總的死亡人數約在1100萬左右。最為寬泛的統計包括600萬蘇聯平民,死亡人數將增加至1700萬人。[275]美國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的研究估計1500-2000萬人死亡或被監禁。[10]R·J·拉梅爾(R.J. Rummel)對納粹國家主導的屠殺行為死亡人數估計為2100萬人。另一估計加上蘇聯平民後的死亡人數達2600萬人。[279]
| 年份 | 猶太受害人[280] |
|---|---|
| 1933–1940 | 少於100,000 |
| 1941 | 1,100,000 |
| 1942 | 2,700,000 |
| 1943 | 500,000 |
| 1944 | 600,000 |
| 1945 | 100,000 |
| 國家 | 估算 戰前 猶太人 人數 |
估算 受害 |
比例 受害 |
|---|---|---|---|
| 波蘭 | 3,300,000 | 3,000,000 | 90 |
| 巴爾幹國家 | 253,000 | 228,000 | 90 |
| 德國與奧地利 | 240,000 | 210,000 | 90 |
| 波西米亞和摩拉維亞 | 90,000 | 80,000 | 89 |
| 斯洛伐克 | 90,000 | 75,000 | 83 |
| 希臘 | 70,000 | 54,000 | 77 |
| 荷蘭 | 140,000 | 105,000 | 75 |
| 匈牙利 | 650,000 | 450,000 | 70 |
| 蘇聯白俄羅斯 | 375,000 | 245,000 | 65 |
| 蘇聯烏克蘭 | 1,500,000 | 900,000 | 60 |
| 比利時 | 65,000 | 40,000 | 60 |
| 南斯拉夫 | 43,000 | 26,000 | 60 |
| 羅馬尼亞 | 600,000 | 300,000 | 50 |
| 挪威 | 2,173 | 890 | 41 |
| 法國 | 350,000 | 90,000 | 26 |
| 保加利亞 | 64,000 | 14,000 | 22 |
| 意大利 | 40,000 | 8,000 | 20 |
| 盧森堡 | 5,000 | 1,000 | 20 |
| 蘇聯俄羅斯 | 975,000 | 107,000 | 11 |
| 丹麥 | 8,000 | 52 | <1 |
| 總計 | 8,861,800 | 5,933,900 | 67 |
1945年以來,最常見的對被屠殺的猶太人人數的估計是600萬人。設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大屠殺遇害者和英雄紀念協會寫道,遇害的猶太人無法精確統計,但已從檔案中找到300萬個被殺害的猶太人姓名,並被放置於遊客中心展示,亦可在網上的中心數據庫查閱。[281][282][283]600萬的數字來源於黨衛隊高級官員阿道夫·艾希曼。紐倫堡審判中的黨衛隊官員威廉·霍特證詞稱:1944年8月,艾希曼告訴他已有600萬猶太人被屠殺,400萬死在集中營,200萬被別動隊槍殺或死於疾病。[284]1953年傑拉爾德·賴特林格(Gerald Reitlinger)所著《最終解決方案》給出了遇害人數的早期估計:4,200,000-4,500,000人之間[285],其他早期估計有勞爾·希爾伯格的5,100,000和Jacob Lestschinsky估計的5,950,000。Yisrael Gutman和Robert Rozett在《猶太人大屠殺百科全書》中估計的人數是5,590,000-5,860,000人之間。[286]柏林工業大學的沃爾夫岡·本茨研究出的人數是5,290,000-6,200,000之間。[287][288]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寫道這些數據的主要來源是戰前和戰後人口統計的對比和納粹關於遣送和屠殺的檔案。 [287]
勞爾·希爾伯格的5,100,000遇害者人數被視為比較保守的估計,他只是用了有據可查的死亡記錄,避免統計學上的調整。[289]他在《歐洲猶太人的毀滅》第三版中寫道,800,000人死於猶太隔都、1,400,000人死於露天槍殺、2,900,000人死在集中營。他估計波蘭猶太人的死亡人數達三百萬人。[290]馬丁·吉爾伯特給出了最少估計5,750,000名猶太人被殺,包括在奧斯維辛被毒死的200萬人。[291]露西·達維多維茲使用戰前的統計數據估計有5,934,000猶太人遇害(參見表格)。[292]
各滅絕營死亡人數超過3,800,000人,其中80-90%都據測是猶太人。死在滅絕營的猶太人占納粹大屠殺所有猶太遇害者人數的一半,波蘭的猶太人幾乎都死在這些滅絕營中。[263]除死在滅絕營的猶太人外,至少有五十萬猶太人在其他集中營死亡,其中包括在德國的幾個主要集中營。這些集中營並非滅絕營,但關押有大量的猶太囚犯,特別是戰爭最後一年納粹從波蘭撤出後。約一百萬人死於這些集中營,有估計至少50%是猶太人,但具體數字不得而知。另外有80萬到100萬猶太人在德國蘇聯佔領區被別動隊殺害。許多人亦因疾病和營養不良,在他們被遣送之前就死在波蘭的猶太隔都中。[293]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較低
德國直接或間接控制的佔領區內共有約800萬到1000萬猶太人,猶太人大屠殺中遇害的600萬人占其中的60%-75%。波蘭的330萬猶太人中有90%被殺。[294]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遇害比例亦達90%,但愛沙尼亞的猶太人成功撤離。1933年德國和奧地利的750,000名猶太人只有約1/4倖存。1939年前雖然許多德國猶太人逃離了德國,但他們主要逃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法國和荷蘭,後期他們被遣送並被屠殺。捷克斯洛伐克、希臘、荷蘭和南斯拉夫的猶太人有70%被殺。羅馬尼亞、比利時和匈牙利的遇害比例為50%-70%。白俄羅斯和烏克蘭與之近似,但數據並不確定。猶太人遇害比例較低的國家有保加利亞、丹麥、法國、意大利和挪威。阿爾巴尼亞是唯一一個在1945年猶太人數量比1939年有顯著增加的德佔國:大約200名當地猶太人和1000名以上的難民通過假證件離開或藏身於60%的穆斯林人口中。[295]另外德國最親密的盟友意大利對猶太人對起德國的行為及政策較溫和[296],導致在1943年意大利戰敗前,大量猶太人逃亡至意大利在法國、南斯拉夫和希臘的佔領區及意大利控制下的阿爾巴尼亞王國。同為軸心國的日本對猶太人的政策有所不同,可參見上海隔都。
1990年代東歐政府檔案開放查閱後,希爾伯格(Hilberg)、達維多維茲和吉爾伯特調整了死亡人數的統計。沃爾夫岡·本茨(Wolfgang Benz)持續多年進行人數的更新工作,他在1999年總結道:
1942年1月萬湖會議上提出的消滅所有歐洲猶太人的任務並未完成,但六百萬遇難者已使大屠殺成為了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罪行。遇難者人數不能準確展現——以下必然是最保守的估計。數字過於概括,但必須展示出來以使人看清種族滅絕的規模:猶太人遇害者中德國佔165,000人、 奧地利65,000人、法國和比利時32,000人、荷蘭超過10萬人、希臘6萬人、南斯拉夫與之數量相同,超過14萬來自捷克斯洛伐克、50萬來自匈牙利、220萬來自蘇聯、270萬來自波蘭。另外還需加上羅馬尼亞和德涅斯特種族屠殺的人數(20萬以上)以及從阿爾巴尼亞、挪威、丹麥、意大利、盧森堡、保加利亞遣送並屠殺的人數。
——沃爾夫岡·本茨,《大屠殺:一位德國歷史學家檢視大屠殺》[297]
大屠殺對意第緒語使用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二戰前,約有1100萬到1300萬人使用意第緒語。[298]大屠殺毀滅了猶太社區,包括世俗的和宗教的,破壞了他們日常生活,導致該語言的使用急轉而下。受害人中約有500萬人(85%)是意第緒語的使用者。[299]就剩餘的非意第緒語使用者,希臘和巴爾幹的拉地諾語使用人口也被破壞,導致這種「猶太——西班牙」語言的絕跡。
| “ |
「這是個存在性問題,因此它將是殘酷無情的種族鬥爭,在此過程中將有2-3千萬斯拉夫人和猶太人因軍事行動和食物供給危機消失。 |
” |
| ——海因里希·希姆萊就巴巴羅薩行動的演說,1941年6月[300] | ||

1942年夏,希姆萊的《東方總計劃》被希特拉一口贊同,包括將斯拉夫人從他們的故土滅絕、流放或奴役,以便為德國定居者提供居住空間;該計劃為期20–30年。[301]
作家、歷史學家多麗絲·L·卑爾根(Bergen)寫到:「和其它納粹文獻一樣,《東部總體計劃》大量使用了委婉語…但不管怎樣,它的意圖是顯而易見的。它將德國對多民族政策之間的關係闡明清楚。德國定居點和東部的德國民族;屠殺斯拉夫人;屠殺猶太人都是同一計劃的組成部分。」[302]
歷史學家威廉·W·哈根(Hagen)稱:
《東部總體計劃》… 預想了東歐目標人口的滅絕尺度:波蘭族 – 85%;白俄羅斯族 – 75%;烏克蘭族 – 65%;捷克族 – 50%。這些巨大的減員是通過「苦役」或飢餓、疾病或控制生育…來實現。當俄羅斯民族被戰爭征服後,將會如計劃所述面臨上述四個斯拉夫語國家同樣的命運。[303]
总结
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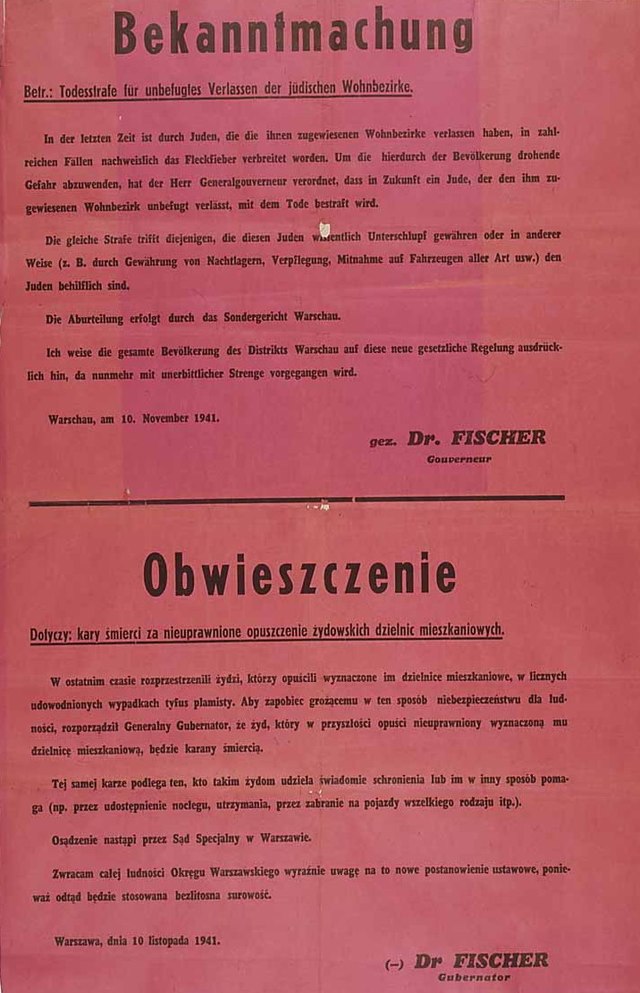

1939年11月,德國人計劃將波蘭人「完全剷除」。[304]「所有波蘭人,」海因里希·希姆萊發誓,「將會從世界上消失。」[305]德控波蘭被要求將波蘭人清除乾淨,以便為德國殖民者騰出地方。[306]到1942年,只有300-400萬人離開波蘭,成了德國定居者的苦工。他們被禁止娶嫁,不能得到醫療救治,直到最後一名波蘭人消失為止。到1939年8月22日,即發動戰爭的一個星期前,希特拉宣佈「戰爭的目標是... 物理地摧毀敵人。這就是為什麼我準備此時只進攻東方,我的『骷髏隊』方案會將所有波蘭後裔和說波蘭語的男人、婦女和兒童殺死,絕不留情。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得到所需的生存空間。」[307]納粹決策者反對對波蘭人進行像對猶太人一樣的大規模屠殺;這在近期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樣一個對波蘭問題的解決方案會在未來成為德國人的負擔,我們的意圖就會被公知於世,至少周邊民族會意識到,他們在某個特定的時間也將遭受同樣的命運。」[308]
屠殺波蘭人的尺度沒有像對猶太人的那麼大。許多波蘭猶太人(約戰前人口的90%)在大屠殺中喪命,而斯拉夫裔信奉基督宗教的波蘭人則倖免於難。[309]有約180萬到210萬非猶太波蘭人在戰爭中遇難,五分之四是波蘭人,餘下的五分之一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少數民族,絕大多數是平民。[265][266]至少有200,000人在集中營遇害,146,000人死於奧斯維辛。許多人在華沙起義後的大屠殺中遇難,約有120,000-200,000人被害。[310][311]
德國對波蘭的滅絕政策包括減少糧食供應、故意破壞衛生、剝奪醫療救助。死亡率從13人/千人上升至18人/千人。[312]總體來說,有二戰遇害人中有560萬人是波蘭人,[266]包括猶太裔和非猶太裔,在戰爭中,波蘭損失了16%的人口;330萬波蘭猶太人中有約310萬人遇害,3170萬非猶太波蘭人中有約200萬人遇害。[313]根據國家紀念院的近期(2009)估算,有超過250萬非猶太波蘭人因德國侵略而遇害。[314]有超過90%的受害人是非軍事死亡的,絕大多數平民是被納粹德國和蘇聯刻意屠殺所致。[310]
1939年8月22日入侵波蘭的前夕,阿道夫·希特拉對他的將軍們說:
成吉思汗屠殺了數以萬計的婦女和兒童——他對此預先謀劃、滿心歡喜。歷史只將他看做了國家的奠基人... 我們的戰爭目標沒有設立特定的標準,而是物理地消滅敵人。由此,我將我的骷髏隊準備妥當——目前只針對東方——將所有波蘭後裔和說波蘭語的男人、婦女和兒童殺死,絕不留情。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得到所需的生存空間。」今天,還有誰提及(土耳其)對亞美尼亞人的滅絕? ... 波蘭得斷子絕孫,為德國人騰出地方。 ... 至於剩下的,先生們,今天我們對波蘭所做的一切,未來俄羅斯的命運也同樣如此。[315][316]
捷克斯洛伐克人也受到了迫害。據估算,約有345,000名捷克斯洛伐克人被殺害,成千上萬人被送往集中營被用作苦工。[317]納粹完全毀滅了利迪策村和萊夏基(Ležáky)村;所有年過16歲的男子被殺,剩餘的人被送往納粹集中營,許多婦女和幾乎所有兒童在那裏離開。
德裔索布人也受到了迫害。
在巴爾幹地區,有將近581,000南斯拉夫人被納粹德國和他們的法西斯同盟及克羅地亞傀儡政權殺害。[318][319]希特拉指使德軍報復塞爾維亞人,後者被認為是次等人類。[320]烏斯塔沙投敵者出於政治、宗教或種族等緣故,製造了系統性的大規模屠殺。許多被害人是塞族人。
波斯尼亞人、克羅地亞人也是亞塞諾瓦茨集中營的犧牲品。美國大屠殺紀念館這樣寫道:
在1941-1945年間,烏斯塔沙政權在克羅地亞建立了大量的集中營。這些營地被用來隔離、屠殺塞族人、猶太人、羅姆人、穆斯林波斯尼亞人、其它非天主教少數民族、以及克羅地亞政治宗教反對派。
美國大屠殺紀念館和猶太虛擬圖書館(Jewish Virtual Library)報道稱有約56,000-97,000人在亞塞諾瓦茨集中營被害。[321][322][323]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報道稱有500,000名塞族人在烏斯塔沙手下以「恐怖暴虐的手段」被剝奪了生命。[324]根據尼哈德·哈利貝格維克(Nihad Halilbegović)最近的研究《亞塞諾瓦茨集中營的波斯尼亞人》(Bošnjaci u Jasenovačkom logoru),有至少103,000名波斯尼亞穆斯林死於納粹和烏斯塔沙手下。根據研究,「死在塞族和克羅地亞同盟手下的波斯尼亞穆斯林人不計其數」,「很多受害人被算為羅姆人」以便提早將其送走。[325][326]
排除意大利控制區的斯洛文尼亞人(意大利仍有對他們進行迫害),有約20,000-25,000名斯洛文尼亞人被納粹或法西斯者殺害。[327]
雖然阿爾巴尼亞為意大利佔領區,但依然與納粹德國合作,其法西斯者對非阿爾巴尼亞人(主要是塞族人)大加迫害。絕大多數暴行由阿爾巴尼亞黨衛隊斯坎德培師(SS Skenderbeg Division)和鮑利·科姆貝塔(Balli Kombëtar)所為。有3,000-10,000名科索沃塞族人被阿爾巴尼亞人殺害,另有30,000-100,000人被流放。[328]


蘇聯公民聚居區也遭到重創。[329]蘇聯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境內有成千上萬的農民被德國部隊殺死。博赫丹·維特維基(Bohdan Wytwycky)估算出大約有四分之一的蘇聯人死在了納粹的手下。[275]
1995年,俄國科學院報道稱蘇聯公民在德軍手下的受害人數(包括猶太人在內)總計為1370萬人,這是德控區6800萬人的20%。這包括740萬被德國屠殺的和報復所致死的人。[262]
在白俄羅斯,納粹德國設立的奧斯蘭總督轄區政權燒掉了約9,000個村莊,將約380,000人用做了苦役,殺死了成千上萬的平民。有超過600村落,如哈廷,則將村莊和其中的所有人一併燒滅,有至少5,295個白俄羅斯定居點被納粹摧毀,其中的平民則多少遇害。提姆·斯奈德稱:「1941年在蘇聯白俄羅斯定居的900萬人中,160萬人被德軍在戰場外屠殺,包括70萬戰俘、50萬猶太人、32萬被列為游擊隊的人(絕大多數是手無寸鐵的平民)。」[330]
德國種族主義者將斯拉夫人與猶太人一道列為最低賤的人種。德國人認為斯拉夫人不適宜接受教育、無法自治、只適合做奴隸以效忠德國主人。希特拉的種族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將斯拉夫人定位為「人口滅絕」。斯拉夫人應被阻止繁衍,被用為苦役。
——露西·達維多維茲(Lucy Dawidowicz),《大屠殺和歷史學家》(The Holocaust and the historians)[331]
邁克·貝倫鮑姆認為在1941年6月到1945年5月,有200-300萬或57%的蘇聯戰俘死於飢餓、虐待或是被處決;絕大多數在第一年被俘時被執行。根據丹尼爾·戈德哈根的估算,有大約280萬蘇聯戰俘在1941-41年間的8個月內離開,到1944年中旬,總計為350萬人。[332]美國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估算出570萬蘇聯戰俘中的330萬人死於德國人手下——不列顛和美國的戰俘犧牲人數為231,000人中的8,300人。[333]當蘇聯戰俘需要幫助德國服奴役時,死亡比例下降;到1943年,50萬人被用於苦工。[264]
| “ | 他們希望把所有骯髒、破敗、怪異的東西都扔進隔離區,他們應該感到恐懼並最終毀滅。 | ” |
| ————伊曼紐爾(Emmanuel Ringelblum)致羅姆人。[334] | ||

由於羅姆人和辛特人是基於口傳歷史而存在的獨立人群,他們受迫害的經歷在記錄上不如其它種族清楚。[335]耶胡達·鮑爾(Yehuda Bauer)寫到記錄不詳可能源自對羅姆人的不信任,以及對他們的侮辱,因為在奧斯維辛的清潔和性接觸冒犯了羅姆禁忌。鮑爾寫到「大多數羅姆人無法將他們的故事與折磨聯繫起來;結果,保持沉默加重了心理創傷的效果。」[336]

納粹佔領區的羅姆政策並不是統一的。有些地方(如盧森堡和波羅的海國家),納粹會將羅姆人口全部滅除。在另一些地區(如丹麥和希臘),則沒有羅姆人被屠殺的記錄。[337]
唐納德·尼維克(Donald Niewyk)和法蘭西斯·尼科西亞(Frances Nicosia)寫到在納粹控制的歐洲,100萬羅姆人和辛特人中至少有130,000人被殺。[335]邁克·貝倫鮑姆(Michael Berenbaum)寫到嚴謹的考證得出的數據是在90,000到220,000人之間。[338]美國大屠殺紀念館高級歷史學家西比爾·彌爾頓(Sybil Milton)的研究計算得出死亡人數至少為220,000人,可能接近500,000人,但這項研究排除了克羅地亞獨立國,而後者對其的屠殺尺度可能極大。[267][339]馬丁·吉爾伯特(Martin Gilbert)估算出在歐洲700,000名羅姆人中大約有220,000人被殺。[340]奧斯丁的德州大學羅姆研究及檔案主任伊恩·漢考克(Ian Hancock)則傾向於大數字,在500,000到1,500,000人之間。[268]漢考克寫到,死亡人數「幾乎肯定地超過了猶太死亡人數。」[341]
在送往集中營之前,受害人被圈進了隔離區,包括華沙隔離區。[121]在東方,成群的別動隊襲擊了羅姆營地,當場進行屠殺,並毀屍滅跡。其它傀儡政權也積極配合,如克羅地亞的烏斯塔沙政權在亞塞諾瓦茨集中營大肆屠殺羅姆人。大屠殺分析學家海倫·費恩(Helen Fein)稱烏斯塔沙幾乎滅絕了克羅地亞的所有羅姆人。[342]
1942年5月,羅姆人被置於與猶太人同等待遇的勞動和社會法案下。1942年12月16日,納粹屠殺的「設計師」黨衛隊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萊[343]下令「吉卜賽雜種(Gypsy Mischlinge)、羅姆人、巴爾幹非德國後裔」需要被送往奧斯維辛,除非他們效忠國防軍。[344]1943年1月29日,另一法案命令將所有德裔羅姆人送往奧斯維辛。
1943年11月15日,希姆萊下令在德控蘇區「『定居的』和『混血的』吉卜賽人被視為國家公民。『游牧的』和『混血的』吉卜賽人則與猶太人同等對待,送入集中營。」[345]鮑爾稱這個舉動反映了納粹對羅姆人的意識形態——雅利安人不能被羅姆血統所污染。[346]
納粹時期德國境內的黑人數量約在5,000-25,000之間,尚不清楚該統計是否包含了亞裔人。[347]根據美國大屠殺紀念館的記述:「1933年至1945年間納粹德國和佔領區黑人經歷了隔離、迫害、醫學實驗、監禁、施以暴力及被殺害等各異的命運。然而,對他們並沒有採取像猶太人及其他群體那般系統化的滅絕行動。」[348]此外,阿非利卡人、柏柏爾人、伊朗人和印度人由於被視為雅利安人種,並未受到迫害。對突厥人、阿拉伯人和南亞人,種族限制有所放寬,他們有些亦被德軍招募。[349] (參見自由阿拉伯軍團、突厥斯坦軍團)
| “ | 我們的起始點不是個人的,我們不關心什麼應該給飢餓的果腹、給口渴的餵水、給赤裸的穿衣——這些不是我們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是全然不同的。它們可以用清晰的句子寫成:我們必須用健康人來佔領世界。 | ” |
| ——1938年,約瑟夫·戈培爾[350] | ||

T4行動在1939年開始,意圖是保持德意志基因的「純潔性」,殺死或閹割有殘疾的或患心理疾病的人。[351]
在1939年到1941年,在心理醫院中有80,000-100,000位心理疾病患者被處死、兒童5,000位;猶太人1,000位。[352]在心理醫院外,人數約為20,000位 (根據安樂死中心哈泰姆城堡(Schloss Hartheim)的副主任格奧爾格·雷諾大夫(Dr. Georg Renno)報告)或400,000位(毛特豪森集中營司Frank Zeireis)。[352]另有300,000人被強制絕育。[353]從總數上來看,約有200,000位有心理疾病的患者被處死,而該數目在歷史上並不受到重視。與物理殘疾的人一樣,患有侏儒症的人也被處死。很多人被關入籠子裏展出,或是被納粹拿來當做實驗品使用。[354]雖然沒有受到正式的參與命令,精神病院和精神病醫生在各個階段都積極配合了這項暴行,以及之後的處理各種「不受歡迎的」人和猶太人。[355]在德國天主教和新教的強烈抗議後,希特拉於1941年8月24日命令取消T4行動。[356]
這項行動的名稱來源於Tiergartenstraße 4,後者是柏林蒂爾加滕(Tiergarten)區一個小別墅的地址,是福利和照顧機構總部的所在地,[357]由菲利普·鮑赫勒和卡爾·勃蘭特領導,前者為希特拉的私人總理(Kanzlei des Führer der NSDAP),後者為希特拉的私人醫生。
1946年12月,勃蘭特與其它22人站在了紐倫堡審判的被告席上,這一案件被稱之為《美國訴卡爾·勃蘭特等人案》,或稱《醫生審判》(Doctors' Trial)。1948年6月2日,勃蘭特在巴伐利亞的蘭茨貝格監獄被執行絞刑。
德國共產黨人、社會主義者和工會主義者是納粹黨人在德國國內最早的敵人,也是首批被送至集中營的群體之一。[358]希特拉稱共產主義是猶太人的學說,並將其稱為「猶太布爾什維主義」。1933年,納粹黨以反對共產黨顛覆的名義頒佈了《授權法案》,該法案授予了希特拉獨裁的權力。戈林在後來的紐倫堡審判中稱,正是納粹黨壓制德國共產黨的意願促成了興登堡總統與德國精英階層同納粹合作。[359]
德國左翼對納粹黨種族主義的反對是納粹憎恨左翼的另一個緣由,德國左派組織的許多領導人是猶太人,猶太領袖在1919年的斯巴達克同盟起義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希特拉將馬克思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視為「國際猶太人」破壞「種族純潔」及雅利安人和北歐人生存的一種手段,另外的原因是他們會激化社會階級矛盾,組織工會反對政府及國有企業。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以及其他集中營中,德國共產黨人相比猶太人享有更多特權,這是因為他們種族更加純潔的緣故。[360]
納粹新佔領區內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者通常是首先被拘留或處決的人群,如希特拉著名的《政委命令》即是一例,他下令凡是被德軍所俘虜的蘇軍政委以及德佔區內所有的共產黨員一律處決。[361][362]別動隊在東部戰線負責執行這些處決。
1941年12月7日,希特拉還簽署了《夜霧命令》,德軍最高統帥部總長威廉·凱特爾予以下發執行,在納粹佔領區中諸多政治活動人士因此命令被綁架而下落不明。

在《我的奮鬥》中,希特拉寫道共濟會已「屈從」於猶太人的掌控之下:「由共濟會宣揚的民族自我保護和平主義論調,被猶太媒體宣傳以麻痹大眾。」[363]1930年代中期前,納粹德國並未將共濟會視為嚴重的威脅。[364]海德里希甚至建立了一個共濟會博物館,艾希曼早年在保安處期間曾於此研究這一被他視為「消失的儀式」。[365][366]另外,希特拉在1938年4月27日頒佈了一個聲明,其中的第三條解除了前共濟會員加入納粹黨的限制,條件是「只要申請人不是共濟會會所的高級別成員」。[367]希特拉始終將共濟會視為一個陰謀組織,但其參與者並未受到如同猶太人那樣的系統迫害。[364][368]集中營中的共濟會成員是以政治犯的身份被關入的,他們佩戴紅色倒三角標誌。[369]
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認為由於許多被捕的共濟會成員也具有猶太人或政治反對派身份,尚不清楚有多少人僅因為其共濟會成員的單一原因被送入納粹集中營。[370]蘇格蘭共濟會總會所估計被處決的共濟會成員約在 80,000 到 200,000 之間。[270]
約12,000名耶和華見證人因拒絕宣誓效忠納粹黨或參軍服役而被迫佩戴紫色三角形,他們被送至集中營,並給予他們放棄信仰、屈服國家權威的選擇。約2500-5000名耶和華見證人被殺害。[274]漢堡諾因加默集中營紀念館主任、歷史學家 Detlef Garbe 寫道:「沒有任何宗教運動能如此堅定一致地頂住壓力,不屈從於國家社會主義。」[371]
德國境內的華人和華裔在1933年到1945年的納粹德國時期儘管沒遭到大規模的屠殺,但納粹黨政府仍對華人進行了系統性的大規模迫害。1941年中華民國對德宣戰,不久後納粹德國政府原本對華人的監控和打壓最終升級為直接迫害。絕大多數華人都被迫離開德國,剩下的則悉數遣送勞改營或集中營,遭到殘酷虐待。截止二戰結束,位於柏林、漢堡、不來梅的所有華人社區均被清除,德國境內已基本沒有華人存在。
獨特性存疑
卑詩省奧肯那根大學教授亞當·瓊斯認為,自1994年盧旺達種族屠殺後,認為猶太人大屠殺具有獨特性的觀點已不再廣泛流傳。[372]
1997年,《共產主義黑皮書》出版後引發了對蘇聯與納粹罪行間進一步的比較。該書認為蘇聯和納粹的罪行間並沒有很大差異,只是納粹的做法比蘇聯激進得多。[373]在猶太大屠殺研究界中,諾曼·芬克爾斯坦寫道大屠殺唯一性的觀點最早出現於1967年的公開談話中,但納粹大屠殺學界並未接受這一觀點。[374]
美國波士頓大學的史蒂文·卡茨認為大屠殺是歷史上唯一的一次種族滅絕行動,並認為「大屠殺」(Holocaust)一詞專指「歐洲猶太人的苦難」,而不包括其他納粹受害者。[375]
參見
依國別
- 阿爾巴尼亞的猶太人大屠殺
- 白俄羅斯的猶太人大屠殺
- 比利時的猶太人大屠殺
- 克羅地亞的猶太人大屠殺
- 愛沙尼亞的猶太人大屠殺
- 法國的猶太人大屠殺
- 拉脫維亞的猶太人大屠殺
- 立陶宛猶太人大屠殺
- 挪威的猶太人大屠殺
- 波蘭的猶太人大屠殺
- 羅馬尼亞的猶太人大屠殺
- 俄羅斯的猶太人大屠殺
- 塞爾維亞的猶太人大屠殺
- 烏克蘭的猶太人大屠殺
- 蘇聯的猶太人大屠殺
受害人與倖存者
- 納粹大屠殺著名倖存者列表
- 納粹大屠殺中的兒童
其它國家的參與
救助者
善後
- 納粹大屠殺的善後
- 去納粹化
- 功能主義與蓄意主義的爭論
- 歷史學家爭論
- 納粹大屠殺罪責
法律回應
- 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
- 阿道夫·艾希曼
- 德國戰爭罪行
- 德國國防軍戰爭罪行
其他觀點
文化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類似事件
註解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