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顿·马瑟(英语:Cotton Mather;/ˈmæðər/ FRS,1663年2月12日—1728年2月13日)是美洲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位清教徒牧师、多产作家、小册子作家与意见领袖,他于1681年取得哈佛学院文学硕士学位,1710年取得格拉斯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虽然马瑟不但在植物杂交种实验上有所贡献,还发扬了接种技术,为科学领域做出了贡献,但现今他主要是知名于在塞勒姆审巫案中的活跃事迹。在审巫案中,马瑟致力于将人定罪为巫师或女巫,并支持使用幽灵证据来为他们定罪。
生平与著作


科顿·马瑟于1663年出生在麻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波士顿,他是因克瑞斯·马瑟和玛丽亚·马瑟(旧姓“科顿”)的儿子。两位著名的清教徒牧师约翰·科顿和理查·马瑟分别是他的祖父和外祖父,而“科顿”这个名字便是为了纪念他的外祖父而取的。
马瑟年轻时曾就读波士顿拉丁语学校。在马瑟死后,这所学校将他的名字列入了学校的名人堂中。1678年,15岁的马瑟毕业于哈佛学院。在完成他的学士后学业后,他回到波士顿,于他父亲就职的北教堂[a]担任助理牧师。1685年,马瑟成为该教堂的本堂牧师[1]:8。
一般认为科顿·马瑟和他父亲因克瑞斯·马瑟之间关系紧张。因克瑞斯曾是北教堂的本堂牧师和哈佛学院的校长,他的人生可说是相当成功。尽管科顿再怎么努力,在政治领域上他始终没办法像他父亲那样成功、知名。只有在作为一名作家的著作数量(超过450本)上,他才胜过他父亲。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塞勒姆审巫案中曾浮上台面,据说因克瑞斯当时并不支持他儿子的举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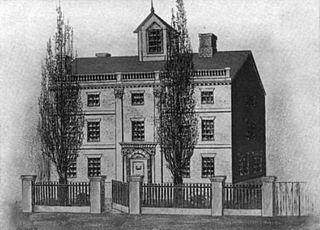
马瑟写下了超过450本书籍和小册子,他的著作在当时的美洲可说是无处不见,使他成为美洲最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之一。他树立了殖民地的道德基准,呼吁自英格兰移民到美洲殖民地的清教徒第二代、第三代回归到清教主义的神学本质。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是《基督在美利坚的荣光造物》(1702年),此著作由七本书组成,分为两卷。

马瑟也对早期美洲的科学发展有所贡献。1716年他主导了一场玉米品种实验,这是有留下纪录的植物杂交种实验中最早的一个。在他寄给朋友詹姆斯·裴蒂弗的一封信中纪录了这场实验的成果[3]:
首先:我的朋友种下一排红色与一排蓝色的印第安玉米;田里其他地方则种下黄色玉米,这是最常见的颜色。在迎风面的田地,红色和蓝色的那两排会感染第三排和第四排,以及一部份的第五排和第六排,使这些玉米转变为和它们相同的颜色。但在背风面的田地,被感染为相同颜色的玉米不少于七或八排,对那些还没转变颜色的玉米也造成了一点影响。[4]
劳勃·波以耳对马瑟的职业生涯影响深远。马瑟在1680年代将波以耳的著作《Considerations touching the Usefulness of Experimental Natural Philosophy》仔细地从头到尾阅读了一遍,他早期的科学与宗教著作受到波以耳很大的影响,著作中的用词几乎都和波以耳相同[5]。
马瑟曾发表过末日预言,预言世界会在1697年迎向末日。预言失败后,他又两度修改了预言中的年份[6]:338。
1713年11月,马瑟的妻子、他俩的两岁大女儿和刚诞生的一对双胞胎全都在麻疹流行期间死亡[7]。这是他第二次丧偶,且他全部15个孩子中只有两个幸免于难。
马瑟曾帮忙说服伊利胡·耶鲁,要他向纽黑文一所即将新建的学校捐款,这所学校就是后来的耶鲁学院[8]。
1728年,他在65岁生日的隔天逝世,遗体被埋在老北教堂旁边的考普山墓地。
塞勒姆审巫案
1689年,马瑟出版了《难忘的远虑──关于巫术与殖民地》(Memorable Providences, Relating to Witchcrafts and Possessions)一书,书中他详细描述了爱尔兰裔洗衣妇安·格罗夫的审巫案,此事件发生在1688年的波士顿,格罗夫被指控对雇主古德温家(Goodwin family)的几个孩子施行巫术,最终也因此被处决[9]。马瑟在这起审巫案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除了替受害的孩子们祈祷、禁食和冥想之外,他也观察并记录下他们的行为举止,并将其详细地刊载在《难忘的远虑》书中。孩子们显然受到歇斯底里的影响[10]。在书中,马瑟主张既然这世上有女巫和恶魔,那当然也会有“不朽的灵魂”(immortal souls)存在。他还说女巫就像它们一样幽灵般地出现[11]。马瑟反对任何以物质层面解释的合适解释,他相信那些承认自己使用巫术的人们有著正常理智,他反对表演魔法,因为那与恶魔有所联系。他认为将幽灵证据纳入法律诉讼是洽当的,但将人定罪不能只基于幽灵证据,因为恶魔也有可能变身成一位无辜人士的模样来作乱[12]。罗伯特·卡里夫是当时批评马瑟的人士之一,他认为马瑟的这本著作为三年后的塞勒姆审巫案奠下基础:
科顿·马瑟先生比起这片土地上其他任何牧师都还要活跃、还要更前线,他将孩子们[b]的其中一位带回家,并和那孩子策划了这等阴谋诡计,在他印出了《难忘的远虑》这样一个事件全纪录后,十分有助于点燃那些火种……[13]
19世纪的历史学家查尔斯·温特沃思·阿珀姆认为塞勒姆审巫案中那些出现奇怪症状的“受害者”们正是在模仿古德温家的孩子们,不过阿珀姆不只责怪科顿,还责怪他的父亲因克瑞斯·马瑟:
对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舆论,他们是有责任的……比起其他任何人都来得多。那的确是一个迷信的年代;但这些迷信很多出自于他们的操作、他们的影响和他们的著作,始于因克瑞斯·马瑟1681年的牧师集会,结束于科顿·马瑟与古德温孩子们的交流,以及他那被广泛传播、印刷的事件纪录。那么,出于这个原因,首先我认为这两人须为所谓的“塞勒姆审巫案”负起责任……[14]
从事件初始起,马瑟就有能力影响法庭对审巫案所做出的解释。当时麻萨诸塞湾省才刚成立没多久,初代省长威廉·菲普斯指派他的副省长威廉·斯托顿主导这个特别的巫术法庭。斯托顿成为殖民地法庭的审判长,负责这起审巫案。根据19世纪的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的说法,在政治界不受欢迎的斯托顿之所以有办法当上威廉·菲普斯的副省长,和科顿·马瑟脱不了关系。马瑟动用他那在政治界活跃的父亲的影响力,干预了此事。班克罗夫特如此写道:“科顿·马瑟为了斯托顿的晋升而向人求情,斯托顿是一个冷酷、骄傲、任性固执且贪图荣誉的男人。”[15]。马瑟显然将这位从未结过婚的单身汉视为他在教会事务上的盟友,班克罗夫特在他的著作中引用了当时马瑟对斯托顿顺利就职时的反应:
“获得帮助的时刻到了。”科顿·马瑟兴高采烈。“是的,定下的时刻到来了。”[16]
马瑟宣称他没有参与塞勒姆审巫案的审判(尽管他的父亲因克瑞斯参与了对乔治·巴勒斯的审判),但与他同时代的罗伯特·卡里夫和汤玛斯·布拉特尔认为他确实影响了几起处决。在审巫案尚未落幕前,马瑟就已经开始宣扬并庆祝这些审判:
“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不满的声音,发表这些审判可能会使我们萌发对上帝的感恩之心,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正义已被执行,我将为增添了光辉的上帝感到喜悦。”
马瑟宣称自己在这起事件中的定位是“历史学家”而非事件的拥护者,但在他的著作中却对被告们的罪行有著强烈的预设立场。他将玛莎·科里安称呼为“一个狂暴的女巫”(a rampant hag),还将乔治·巴勒斯称为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男人”(very puny man)[c],还说巴勒斯那“搪塞、矛盾且有谬误”的证词“并不值得考虑”[17][18]。
作为原告的受折磨女孩们会宣称被告以“灵体”的形式攻击他们,这些证言在塞勒姆审巫案中常常被视为是可供采信的证据,此即所谓的“幽灵证据”。举个例子,女孩们可能会说“伊莉莎白·普罗克特咬我、掐我,想害我窒息!”,即使这所谓的攻击事件实际上是发生在她们的梦或幻觉中,即使她们所看到的攻击者只不过是和被告的外型有那么点类似,也会被解释成“女巫转变成灵体形式进入梦中攻击她们”。
1692年5月31日,马瑟写信给审巫案的法官之一,同时也是他教堂所属会众的约翰·理察兹。马瑟在信中表示自己支持这次起诉,但还是要提醒他:
“幽灵证据的使用不要超过它应有的限度……毫无疑问的,魔鬼不只会化成那些无辜人士的形体,也可能会变成那些道德高尚的人士。虽然我相信公正的上帝通常会透过某种方法来迅速证明他们的无罪。”[19]
地方上的牧师们对此议题发表了意见,他们于1692年6月15日给出回复,在这些回复当中,马瑟似乎收到了不少正面回馈:
“据我所知,年轻的科顿·马瑟正写出了他们的渴望。”[20]
在《数名牧师的回复》(Return of the Several Ministers)中,矛盾地论述了是否该允许幽灵证据的使用。信件的原始完整版本经过翻印后,被收录在1692年因克瑞斯·马瑟所著《良心案》(Cases of Conscience)的最后两页。这是一份奇怪的文件,将这充斥著混乱与争执的资料来源保存了下来。卡里夫称之为:
“完美的两面讨好手法,先是鼓励使用那些邪恶的方法,再给予他们警告……确实,这些建议看起来很像他的著作中会出现的东西,一方面带来火源以增长火势,一方面又带来水以熄灭大火。”[21][22]
似乎有几名与其商议的牧师并不同意使用幽灵证据,这也是为什么科顿·马瑟此时给出的解释和建议至关重要。汤玛斯·哈钦森为《数名牧师的回复》一文做出总结:
五年后,马瑟以匿名发表的《菲普斯的人生》(Life of Phips,1697年)中收录了《数名牧师的回复》的翻印文,并刻意省略掉了最关键的“首两段与最后那段”,虽然这几段在他1692年初秋贸然出版的《未知世界的困惑》中也有收录,早已获得了许多关注。
1692年8月19日,马瑟在场参与了乔治·巴勒斯(与同时处刑的其他四人)的处刑[23],卡里夫称马瑟在这次处刑中扮演著直接且重要的角色:
| “ | 乔治·巴勒斯和其他人一起被关在囚车里,通过塞勒姆的大街,押赴刑场。在他即将行刑的时候,他向众人做最后的演说,声明自己无罪。如此庄重严肃的演讲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他的祷文措辞极佳,演讲时极为沉著冷静。他的演说如此动人,很多人的眼泪都流了下来,看起来这场行刑很有可能被观众打断。这时,原告站出来说,有魔鬼在指示他说这些。在他被吊死后,科顿·马瑟一跃上马,大声向民众演讲,一边说巴勒斯先生是未受任命的牧师,一边向大家诉说他的罪行,他说魔鬼经常会以光之天使的形体出现。这确实稍微安抚了民众,剩下的行刑得以继续。巴勒斯先生的绞索被砍断,(某人)抓住他的绞索,将他的尸体拖到一个坑中,或一个坟墓中,在两英尺深的岩石之间。他的上半身和屁股被扒光,一条受刑人的旧裤子被放在他的下半身上。他被放了进去,和玛莎·科里安与约翰·威拉德葬在一起,他的一只手、下巴和一只脚曝露在外。 | ” |
| ——罗伯特·卡里夫《未知世界的更多困惑》 | ||

1692年9月2日,由于已有11名被告遭处决,科顿·马瑟写了封信向审判长威廉·斯托顿祝贺,说他“绝妙地消灭了恶魔的功绩已被世间知晓”,但也表示“然而,有一半是出自我的努力,这点却没有被世界看见。”
有关马瑟和幽灵证据的关系,查尔斯·温特沃思·阿珀姆做出了以下结论:
科顿·马瑟从未在公开发表的著作中谴责幽灵证据“被许可使用”的问题,也从未建议要全面地排除幽灵证据的使用:相反的,他却承认那是一种可被推定的根据……(而一旦它被承认,)没有任何论点敌的过它。人格、动机、常识,全被一扫而空。[24]
波士顿的知识份子、马瑟的批评者汤玛斯·布拉特尔在1692年一封写给一位英格兰神职人员的信中,批评了那些使用幽灵证据的法官:
塞勒姆的绅士们绝不会允许任何人因为幽灵证据而被判有罪并受到谴责……但关于是否就算没有幽灵证据,人们也会被判有罪的问题,我将这交由你与其他有辨别能力的人们自己判断。[25]
后来人们开始议论,说省长威廉·菲普斯的妻子玛丽或许也涉及了巫术。与此同时,省长菲普斯决定下令杜绝幽灵证据的使用,此时是1693年1月。菲普斯的决定缓解了局势,这马上让女巫们被定罪的机率大幅下降,在这之后也不再有人被当成女巫处决。菲普斯的这个决定受到了副省长斯托顿的强烈反对[24]。
乔治·班克罗夫特在著作中提到,科顿·马瑟认为女巫就在那些“贫穷、卑微、衣衫褴褛的乞丐”当中。班克罗夫特断言道,马瑟认为那些反对女巫审判的人,都是女巫的拥护者[26]。


作为此次事件的主要推动者,在审巫案结束后,马瑟和威廉·斯托顿都不同意那些针对他们的强烈疑虑。在审巫案结束后的头几年,马瑟持续为他们二人辩白,他似乎仍然认为他们还有机会回归[27]:67。
马瑟在他的著作《未知世界的困惑》中描写了他的布道、殖民地的现况与欧洲的女巫审判[28]:335。书中也稍微澄清了他在《数名牧师的回复》一文中对于幽灵证据的使用所提出的自相矛盾建议。透过这次的澄清,他表示自己是支持使用幽灵证据的[29]。
《未知世界的困惑》的发行时间与他父亲因克瑞斯的《良心案》(Cases of Conscience)相差无几[30]。马瑟起初并不支持他父亲的著作:
有14位值得尊敬的牧师最近正著手写书并发表到报刊上,其中包含了和巫术有关的《良心案》。我凭我的良心思考……〔中间省略〕……这些发言永远地扼杀掉了任何更进一步的司法程序,还会使针对法官的公开质疑越来越多……
——1692年10月20日,给舅舅约翰·科顿的信[31]
梅西·肖特(Mercy Short)及玛格丽特·鲁尔(Margaret Rule)是塞勒姆审巫案的原告,马瑟分别于1692年12月和1693年9月拜访了这二人,这是马瑟所涉及的最后几次与巫术相关的较大事件[32]。受到“马瑟拜访鲁尔事件”的刺激,罗伯特·卡里夫推动了一场为期五年的“反马瑟运动”,反对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马瑟[30]。卡里夫写下了《未知世界的更多困惑》(More Wonders of the Invisible World)一书,写作动机是为了要重新见证1692年的那场可怕事件,并担忧马瑟可能会“再度成功地掀起一场审巫案”。他在书中引用了陪审团和其中一个涉案法官的公开道歉。因克瑞斯·马瑟后来被撤下哈佛校长的职位,并由塞缪尔·威拉德取而代之。据说因克瑞斯差不多在同个时期公开地在哈佛园中烧毁了卡里夫的著作[33][34]。
天花接种争议
天花接种(smallpox inoculation)——不同于之后才发展起来的疫苗接种(vaccination)——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8世纪的印度[35]或10世纪的中国[36]。此技术大约也在17世纪时于土耳其兴盛起来,更确切的说,在土耳其所使用的是“人痘接种”(variolation),此技术透过使用症状较轻微的天花患者的分泌物,来制造出可控制且容易痊愈的感染,让身体得以产生抗体。18世纪初,英格兰的皇家学会曾讨论过是否该引进天花接种技术,而1713年的天花疫情又更进一步地提升了学者们对此技术的兴趣[37]。然而一直到1721年,在英格兰的美洲殖民地才出现了英格兰第一起有纪录的接种病例[38]。
天花在殖民美洲是相当危险的疾病,它具有高度的接触传染性,且死亡率高达百分之30[39]。虽然最蒙受其害的是美洲原住民,但英裔白人也同样地为此困扰。新英格兰在1677年、1689-1690年和1702年都有爆发过天花流行疫情[40],其中波士顿的天花疫情则是流行于1690年和1702年。在此期间,麻萨诸塞的公家机构主要透过实施隔离来处理疫情。入境的船只会在波士顿港口被隔离,镇上的天花病患要不被严加看管,要不被送入“隔离病院”(pesthouse)内[41]。
1706年,马瑟的非裔奴隶阿尼西母告诉马瑟,童年时期他在非洲是如何被接种的[42]。马瑟深深地被这个想法所吸引。1716年7月,他在《自然科学会报》上读到了君士坦丁堡的伊曼纽·蒂莫努斯医生(Dr. Emanuel Timonius)对于接种技术的赞同。马瑟随后在写给伦敦格雷舍姆学院的约翰·伍德沃德博士的一封信中表示,假如殖民地再度爆发天花疫情的话,它会极力催促波士顿的医生采用天花接种技术[43]。
到了1721年,年轻一代的波士顿人都没有经历过天花疫情,他们基本上并不害怕天花[44]。同年4月22日,英国海军船舰“海马号”(HMS Seahorse)带著天花病原,从西印度群岛返回港口。尽管当时的人们试图通过隔离来保护城镇居民,但到了5月27日,波士顿已经出现了八起天花病例。截至六月中旬,该疾病以惊人的速度蔓延。随著新一波的天花疫情持续蔓延,许多居民也逃到了较偏僻的农村。人口外流、隔离、外来贸易对象的恐慌等种种问题一同袭来,在这殖民地的首都闹得人仰马翻。卫兵驻扎在众议院,以防任何未经特别许可的波士顿人进入。到了九月份,死亡人数来到101人,而市政委员们对此根本无能为力。据说情况已经糟到“要严格地限制丧钟可被敲响的时间长度”[45]。
1721年6月6日,马瑟将蒂莫努斯医生和雅各布斯·派拉蕊纳斯(Jacobus Pylarinus)所写的接种报告书的内容摘要寄给当地的医生们看,敦促他们商议此事,但他没有得到回应。接著,马瑟将接种技术引介给扎布迪尔·博伊尔斯顿医生使用,博伊尔斯顿尝试为他13岁的小儿子和两名奴隶(一名成人和一名小孩)进行接种,三个人都在大约一周内康复,这是美洲最初的接种案例。有了这些成功的经验,博伊尔斯顿又在七月中旬为至少七人进行接种。天花疫情于1721年10月达到巅峰,有411人死亡。一直到1722年2月26日,波士顿才终于摆脱了天花。从1721年4月开始算起,病例总数达到5889例,其中有844例死亡,超过四分之三是死于1721年[46]。与此同时,博伊尔斯顿为287人进行接种,其中只有6人死亡[47]。
博伊尔斯顿医生和马瑟的大规模接种在波士顿掀起了一场可怕的喧嚣[48]。马瑟在他的日记中承认,他们二人是“人们愤怒的对象;他们对此破口大骂并恶言相向”。波士顿的市政委员们将医生找来,声称这种做法已造成多人死亡,只会害疾病继续扩散而已,要博伊尔斯顿不要再这么做了[49]。
《新英格兰新闻》上刊载了反对此作法的声音。根据这家报刊所刊载的内容,波士顿的民众担心接种不但不会阻止疾病的扩散,反而还会助长它。不过,有些历史学家,如H·W·布兰德斯认为这是因为报刊的总编辑詹姆斯·富兰克林(班杰明·富兰克林的哥哥)站在反对立场[50]。反对舆论的源头是波士顿的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他提出了条理分明的反对论点,说明天花接种违反医学原则[51]。包括约翰·威廉斯在内的几位反对人士认为,天花接种的实施违反了医学的自然规律,让医生从治疗他人者转变为伤害他人者[52]。如同大多数的殖民地居民,威廉斯生活中的各部分都深刻地受到了清教徒信仰的影响,在此案件中,他也引用了圣经来强调他的论点。他所引用的章节是《马太福音》9:12,“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著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甚至在1721年11月,还有某个极端份子朝马瑟的家投掷一颗引信已经点燃的手榴弹[53][54]。
一般来说,清教徒牧师们是支持接种试验的。如因克瑞斯·马瑟就和其他两位著名牧师,班杰明·柯尔曼(Benjamin Colman)与威廉·库珀(William Cooper)一起公开宣扬接种的使用[55]。“其中一个清教徒思想的典型假说是,要在自然和神启中辨别何谓上帝的旨意。”[56]
然而,约翰·威廉斯却质疑天花“并非上帝的奇怪杰作”。他还问他的读者,上帝是否把将天花传染给人们视为一种“对罪恶的惩罚”,并警告透过接种来试图保护自己免受上帝的愤怒,只会“更加激怒祂”[57]。
清教徒在苦难中寻找意义,他们还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透过天花来表达对他们的不满。在尝试治疗前若不先矫正人们所犯下的错误,可能只会让人们“回归宿命”。许多清教徒相信接种的做法:先制造伤口再放入病菌,是一种暴力行为,与美好的治疗行为大相迳庭。他们努力遵守十诫,成为合乎体统的教会成员与善良又关怀人心的邻居。以接种为由伤害或谋杀邻居,显然和十诫中的第六诫:“不可谋杀”矛盾,这成为了反对方的主要意见之一。威廉斯认为,由于在圣经中无法找到支持接种的理由,这便不是上帝的旨意,因此是“非法的”[58]。由于清教徒普遍透过圣经来决定所有决策,缺乏经文的支持便会让许多人心怀疑虑。威廉斯畅所欲言的奚落马瑟,因为他没办法从圣经中引用经文来支持接种[59]。
波士顿的威廉·道格拉斯医生为此议题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The Abuses and Scandals of Some Late Pamphlets in Favour of Inoculation of the Small Pox》(1721年),讲述了有关天花接种的滥用与丑闻。道格拉斯医生曾在欧洲取得了医学学位,以当时的人来说相当优秀。
道格拉斯医生以较为世俗的论点来反对天花接种,他强调理性比感性重要,并力劝大众做出务实性的选择。此外,他要求牧师们应该让医生来实践医学行为,因为牧师们缺乏该领域所需的专业知识。根据道格拉斯医生的看法,天花接种是一个“重大的医学实验”,不能轻易实施。他认为,并非所有学识渊博的人都能够胜任医治他人的职责,虽然在殖民地早期历史中,包括照顾病人在内,牧师常常要身兼多职,但现在他们被认为应该要远离政府和俗事。道格拉斯认为接种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达到预防效果的人数。道格拉斯说,马瑟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把这技术用在小孩子身上,而孩子们自然比大人更能够迅速恢复体力。道格拉斯总是立誓要对抗“散播传染病的邪恶”[60]。文献上记载著:“这两位有名望的敌手(道格拉斯和马瑟)之间争斗的时间远远长于传染病本身流行的时间,伴随著这段争议所产生的文献既庞大又充满恶意。”[61]
随著天花疫情的扩大,死亡人数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找出危机的解决方案已是刻不容缓。人们尝试了诸如隔离和体液学说等许多方案,但都没有成功减缓疾病的传播。消息从一个城镇传到另一个城镇,甚至传到了海外,有关天花的恐怖故事造成了人们的大规模恐慌。“到了1700年左右,天花已经成为了大西洋两岸最具毁灭性的流行疾病。”[62]
马瑟强烈反对那些认为接种违背上帝旨意的观点,他认为这种做法并不违反清教徒的常规。他写道:
一名基督徒是否可以不使用这份良药(让这麻烦事成为将会发生的事)并谦卑地感谢上帝让他们在这悲惨世界中发现祂的良善天意;并恭顺地为这良善天意感到钦佩(就像我们在使用其他任何良药时做的一样)?这似乎挺奇怪的,任何聪明的基督徒都无法回答这点。那些自称是医生的人在透过恶言谩骂反对此事时,也等同背叛了他们的解剖学、哲学与神学,这是多么奇怪的事?[63]
清教徒牧师们开始接受这种观点:不管你是好人还是恶人,天花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无可避免的,但上帝却还是为他们提供了自救的手段。马瑟如此写道:“使用过这种技术的人没有任何一位死于天花,与此同时,这疾病是如此致命,至少有一半的人都死了,而他们是透过普通的传染途径(而非因为接种)被传染。”[64]
当马瑟正在实验这种新做法时,著名的清教徒牧师班杰明·柯尔曼与威廉·库珀以神学的角度公开地表达他们对此事的支持[65][66]。
虽然马瑟和博伊尔斯顿能够证明这种做法是有效的,但有关接种的争议还是一直持续到1721-1722年天花疫情结束后。透过第一手经验的分享与人们之间的口耳相传,天花接种技术最后终于被大众所接受。虽然许多人一开始都对天花接种抱持著保守的态度,但由于人们能够在自己的公众社区中不断地见证这种做法带来的正面成果,它最终得以被广泛使用[67]。
在克服了大量难题并获得显著成功之后,博伊尔斯顿于1725年前往伦敦发表成果,并顺利在1726年被选为皇家学会的会员。马瑟本人则是在两年前就取得了会员资格[68]。
向海盗传道
在马瑟的牧师生涯中,他也热衷于向那些已被关押的海盗们布道[69]。他写了许多以“对海盗的传道”为主题的小册子,例如《Faithful Warnings to prevent Fearful Judgments》、《Instructions to the Living, from the Condition of the Dead》、《The Converted Sinner ... A Sermon Preached in Boston, May 31, 1724, In the Hearing and at the Desire of certain Pirates》、《A Brief Discourse occasioned by a Tragical Spectacle of a Number of Miserables under Sentence of Death for Piracy》、《Useful Remarks. An Essay upon Remarkables in the Way of Wicked Men》和《The Vial Poured Out Upon the Sea》。他的父亲因克瑞斯曾在荷兰籍海盗彼得·厚德里厚的审判上传道[70]。科顿·马瑟曾依序在以下这些海盗的审判或处刑上传道:威廉·弗赖、约翰·奎尔奇、塞缪尔·贝拉米、威廉·基德、查尔斯·哈里斯和约翰·菲利普斯。他曾作为一名牧师为海盗汤玛斯·霍金斯、汤玛斯·庞德和威廉·考沃德等人服务,这些人当时和“好主妇”安·格罗夫的女儿,审巫案被告“爱尔兰天主教徒女巫”玛丽·格罗夫关在一起,她受审时马瑟也在场传道[71]。
在与威廉·弗赖及其船员的传道中,马瑟责备他们:
你们心中会有某种东西迫使你们承认,你们所做的事情是最不讲理且最可恶的。你们已承认犯下了抢劫与海盗罪,你无法用任何言词来为这些事辩解。……〔中间省略〕……这是你们所累积的大量罪过中最丑陋的部分,你们被指控犯下一起令人毛骨悚然的谋杀案,从天堂向你们袭来的是血淋淋的呐喊。[72]
著作列表
科顿·马瑟一生中写下大量文章与著作,此处仅列出其中一部分较为知名的文章。
- 主要著作
- 《波士顿星历表》(Boston Ephemeris,1686年)
- 《Ornaments for the Daughters of Zion》(1692年)
- 《未知世界的困惑》(1693年)
- 《圣经中的美洲》(The Biblia Americana,1693年-1728年)
- 《Decennium Luctuosom: a History of the Long War》(1699年)
- 《盐之柱》(Pillars of Salt,1699年)
- 《基督在美利坚的荣光造物》(1702年)
- 《The Negro Christianized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1706年)
- 《Corderius Americanus: A Discourse on the Good Education of Children》(1708年)
- 《Bonifacius》(1710年)
- 《Theopolis Americana: An Essay on the Golden Street of the Holy City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1710年)
- 《基督徒哲学家》(The Christian Philosopher,1721年)
- 《Manductio ad Ministerium》(1726年)
《波士顿星历表》(Boston Ephemeris)是马瑟于1686年所编写的年鉴,内容类似于今日广为人知的《农夫年历》。这份年鉴中包含了大量的天文学内容,当中需要用到大量的计算来算出天体的运动和位置,这表示马瑟对数学也略有涉略[73]。
马瑟过世时留下了大量未完成的遗稿,其中便包括这篇《圣经中的美洲》(The Biblia Americana)。马瑟相信《圣经中的美洲》将会是他写作生涯中最出色的作品,一部杰作[74]。《圣经中的美洲》包含了马瑟对圣经的思想和观点,以及他如何解释这些观点。此著作难以置信地庞大,马瑟从1693年起便著手写作,一直到1728年他过世为止都还没完成。马瑟试著说服他人,哲学和科学能够与宗教相容,而不是互相排斥。人们不需要选边站。在《圣经中的美洲》中,马瑟透过科学的观点来研究圣经,这正好和他在《基督徒哲学家》中的观点完全相反,在后者中,他以宗教的观点去看待科学[75]。
马瑟于1686年发表了他的第一次布道,内容涉及因被判谋杀罪而被处刑的詹姆斯·摩根(James Morgan)。13年后,这次布道的内容经过马瑟的编辑,与马瑟的其他相似作品一同出版,题名为《盐之柱》(Pillars of Salt)[76]。
《基督在美利坚的荣光造物》被认为是马瑟最杰出的著作,出版于1702年,当时马瑟39岁。这本书收录了几名“圣徒”(saints)的传记,并描写了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发展[77]。这边提到的“圣徒”指的并不是天主教教会所定义的圣人,而是指那些马瑟在书中提到的清教徒牧师。
《基督在美利坚的荣光造物》总共由七本书组成,包括他曾于1697年在伦敦以匿名形式出版的《Pietas in Patriam: The life of His Excellency Sir William Phips》。评论家们赞美了这本书,说这本书正确地纪录下美洲殖民地的建立以及当地人民的发展,是此类型书籍中成果最好的之一[78]。
1721年,马瑟出版了《基督徒哲学家》(The Christian Philosopher),这是美洲第一部有系统的科学著作。马瑟试图在书中展现出牛顿式科学和宗教之间是如何和谐共处的。书中有部分理论是基于劳勃·波以耳的《基督徒的品德》(1690年)。
此书还有一部分灵感来自于12世纪的小说《自修的哲学家》,作者为伊斯兰哲学家伊本·图菲利。虽然马瑟将伊斯兰教批评为异教,但他还是将这部小说的主角哈义·伊本·叶格赞(Hayy ibn Yaqdhan)视为基督教哲学家和一神论科学家的理想典范。马瑟认为哈义是一位“高贵野蛮人”,并试图透过哈义的例子来了解美洲原住民,马瑟认为这有助于将美洲原住民转变为清教徒。
参考文献
脚注
外部链接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