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问题
时间线
聊天
视角
伯納德·威廉姆斯
英国哲学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Remove ads
伯納德·亞瑟·歐文·威廉姆斯爵士(英語:Sir Bernard Arthur Owen Williams,1929年9月21日—2003年6月10日),英國道德哲學家,被《泰晤士報》稱為「他那個時代中最傑出、最重要的英國道德哲學家」。[1]他的著作包括《個人問題》(Problems of the Self,1973年)、《道德運氣》(Moral Luck,1981年)、《倫理學和哲學的邊界》(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1985年)、《真理與真誠》(Truth And Truthfulness: An Essay In Genealogy,2002年)等。
作為劍橋大學騎士橋哲學教授(Knightbridge Professor of Philosophy)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多伊奇哲學教授(Deutsch Professor of Philosophy),威廉姆斯在全球範圍內都有着很高的知名度。他最為人所熟知的,是他試圖用歷史與文化、政治學與心理學、特別是希臘文化來重新調整道德哲學研究的方向。[2]他被稱為是「擁有人道主義者靈魂的分析哲學家」,[3]而他則視自己是一個綜合者,將不同領域內看似互不相通的概念融合在一起。他反對科學與進化論的還原論思想,並稱那些「道德上缺乏想像力」的還原論者是「我真正不喜歡的人」。[4]對於威廉姆斯來說,複雜性是不能還原的,它們是美麗而富有意義的。
他支持女性在學術界中的發展,[5]他從她們當中看到了在分析哲學中所無法理解的一種將理智與情感相互綜合的可能性。美國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稱他是「他那一代男人中最為接近女性主義者的」。[5]同時,他也以其犀利的談吐而著稱,牛津大學哲學家吉爾伯特·賴爾有一次評價道,「他比你還清楚你接下來要談的內容,在你還沒有說完整句話前,他就想到了對你的觀點所有可能的反對意見,以及對這些所有可能反對意見的所有解答」。[6]
Remove ads
生活
威廉姆斯出生於英國埃塞克斯郡濱海韋斯特克利夫(Westcliff-on-Sea),是一個公務員的獨子。他曾就讀於奇格威爾學校(Chigwell School),後來到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學習古典人文科學,並於1951年以罕見的第一級榮譽學位畢業。[1]之後,他加入英國皇家空軍服役一年,還曾前往加拿大駕駛噴火戰鬥機。[6]
之後在紐約休假的途中,他結識了其後來的妻子雪莉(Shirley Williams)。雪莉是政治科學家、哲學家喬治·凱特林(George Catlin)與小說家維拉·布里頓(Vera Brittain)的女兒,當時正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在1951年22歲那年獲得牛津大學萬靈學院獎學金後,威廉姆斯與雪莉一起回到英國開始從事研究工作。他們於1955年結婚。[6]後來,威廉姆斯被授予了爵位,而雪莉則被授予終身貴族,他們也成為了少數兩人都憑自身努力而獲得英國貴族稱號的夫妻。
Remove ads
总结
视角

為了滿足妻子的政治抱負,威廉姆斯離開牛津大學,來到了倫敦大學學院。從1959年開始到1964年為止他都在這裏工作,還當選了貝德福德學院(Bedford College)哲學教授。與此同時,他的妻子則是《金融時報》的一名記者。在與妻子17年的婚姻中,他們與文稿代理人希拉里·魯賓斯坦(Hilary Rubinstein)夫婦同住在肯辛頓的一處大房子中。在這段威廉姆斯稱作他一生中最為幸福的時間裏,他與妻子育有一個女兒,名為麗貝卡(Rebecca)。然而,妻子政治生涯的不斷發展使他們二人聚少離多,個人價值觀的不同更是為他們之間的關係蒙上了陰影——威廉姆斯是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而他的妻子則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在他與當時還是歷史學家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妻子的帕特麗夏·勞·斯金納(Patricia Law Skinner)的外遇之後,他們兩人的婚姻也走向了終點。1974年兩人離婚後,威廉姆斯與斯金納成婚,並育有兩子。[6]雪莉·威廉姆斯曾這樣評價他們的婚姻:
……有兩件事造成了我們之間的緊張關係。一是我們都過於關注我們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導致我們無法有更多的時間在一起;另一點,坦率地說,我自己並不傾向於對別人作出判斷,而伯納德則不同,對於他認為是愚蠢而無法接受的人,他會展現出他的才能極為犀利地貶低這些人。帕特麗夏在這一點上比我更聰明,她不會過問這些事。他有時是很令人苦惱的,他對某些人完全不留情面,只當那些人是死人一般。他就像法官一樣,是不會讓別人對他下判斷的。我受到了基督教思維的影響,他就會說「這些東西完完全全都是虛誇的,沒有一點意義」。於是,在關於天主教的問題上我們一直在爭吵。[6]
威廉姆斯承認他有時會很頑固。「我在自傲時我通常會那樣。在哲學上,那些矯矜總會激怒我,特別是那種科學的矯矜。」[6]1967年,他被任命為劍橋大學騎士橋哲學教授。1979年至1987年間,擔任劍橋大學國王學院院長。[1]1988年他離開英國,來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多伊奇哲學教授,有人便以此來證明美國學術比起英國更為繁榮,將他的出走稱為從英國學術界到美國學術界的「人才外流」。某一次他曾一家英國報紙對說,以他身為一名學者的薪水都很難在倫敦市中心買一套房子。2002年11月,他告訴《衛報》,他很遺憾他的出走變得人盡皆知:「有人曾勸說我,當時的學術條件有着很嚴重的問題,我的出走能夠使這種情況引起大眾的注意。結果是這雖然確起到了一點作用,但卻顯得我脾氣很壞,而在我三年後回來時情況變得更無法理解——我與其他人住在一起時感覺同他們難以相處。」[6]
在伯克利期間(1986年至2003年),他曾先後擔任過米爾斯教授(Mills Professor,1986年至1988年)、薩瑟古典講師(Sather Classics Lecturer)和薩瑟教授(Sather Professor,1988年至1989年)[7]以及夢露·多伊奇哲學教授(Monroe Deutsch Professor of Philosophy,1988年至2003年)。[8]同時,他還擔任牛津大學道德哲學懷特教授(White's Professor of Moral Philosophy,1990年至1996年),並於1997年再次任職於萬靈學院。[6]
在學術工作之外,威廉姆斯還在一些皇家委員會與政府委員會中擔任主席。1970年代,他任淫穢與電影審查委員會(Committee on Obscenity and Film Censorship)主席。1979年委員會報告中曾這樣寫道:「根據對流通作品中那些詳盡的性描寫以及它們所造成後果的研究表明,色情作品與性犯罪或者謀殺之間完全找不到任何聯繫。」[2]委員會的這一報告被認為是受到了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自由思想的影響。而密爾則是威廉姆斯非常崇敬的一位哲學家,他將密爾的傷害原則應用到了委員會的研究之中,認為「沒有行為可以被法律所壓制,除非這一行為傷害到了其他人」。[6]
威廉姆斯總結到,色情並不能視為是有害的,「色情並沒有對社會造成重要的影響……擴大色情造成的問題會掩蓋今天我們社會遇到的許多其他問題」。委員會的報告還稱,只要讓兒童無法接觸到色情作品,成人應該被充許自由地去看他們認為適合的色情作品。[6]除了色情之外,他還在有關賭博、濫用藥物、私立學校等問題的委員會中任主席。對此他自己曾說,「所有那些主要的惡習都和我有關」。[1]
Remove ads
從15歲開始威廉姆斯就對歌劇產生了興趣,他曾在英國國家歌劇院(English National Opera)理事會中任職長達20年。[8][9]他還為葛洛夫音樂百科全書(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撰寫了「歌劇」條目,而由他的遺孀帕特麗夏為他編輯的論文集《論歌劇》(On Opera)也已於2006年出版。[10][11]
威廉姆斯1999年被授予騎士爵位。[12]他還是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與美國文理科學院榮譽院士。[8]2000年,劍橋大學授予他榮譽文學博士學位。[1]
2003年6月10日,他在羅馬度假時去世。之前,他一直患有一種惡性腫瘤——多發性骨髓瘤。在他的妻子帕特麗夏與兩個兒子、以及他與前妻的女兒的陪同下,他度過了生命的最後階段。[1]
學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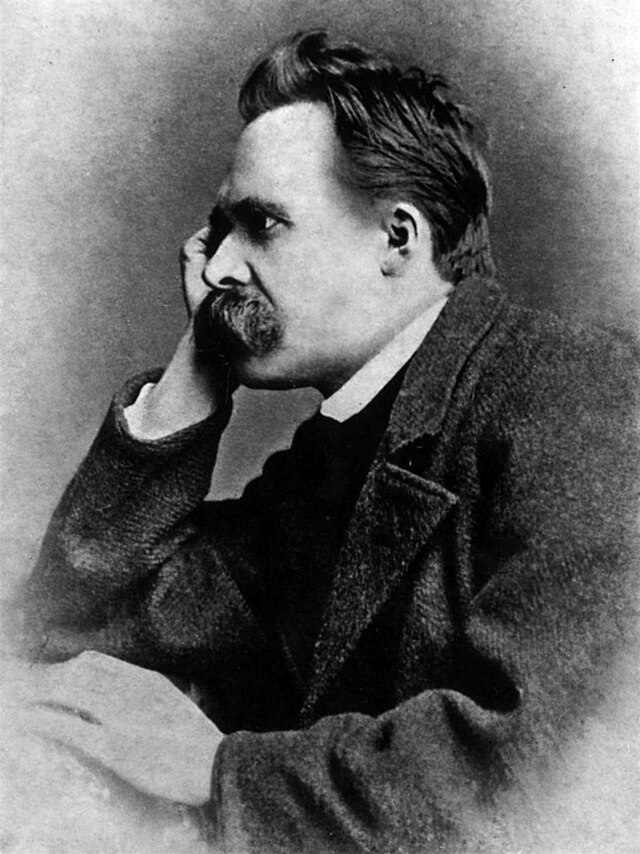
在《道德:倫理學導論》(Mor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s,1972年)一書中,他寫到「大多數時代的大多數道德哲學都是空洞與無趣的......當代的道德哲學則找到一條新的無趣的道路,那就是不探討任何的道德話題」。他認為道德哲學的研究應該更生動、更具有吸引力。他希望找到一種可能被心理學、歷史學、政治學與文化所解釋的道德哲學。在他對道德的批評中,他把道德稱為「一種奇特的制度」(a peculiar institution),認為這種意義上的道德就是把道德看成了一種與人類思想其他方面相分離的東西。有人認為他與19世紀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尼采觀點相似,不過相對而言尼采則持一種完全反對和抱怨的態度,如他在《瞧!這個人》(Ecce Homo)最後所寫的「以一個好人的概念來看,共同原因是由它自身所有軟弱的、噁心的、疾病的、痛苦的東西組成的」。儘管威廉姆斯最初認為這位德國哲學家是一個拙劣的還原論者,但後來他變得十分欣賞尼采,有一次甚至說他希望每20分鐘就引用一次尼采。[10]
儘管威廉姆斯對還原論的牴觸使他看起來是一個道德相對主義者,不過他在《倫理學和哲學的邊界》(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一書中將道德概念可以分為了厚概念和薄概念。其中前者包括「勇敢」、「殘暴」等包含了描述性信息的概念,他認為關於這些概念的探討是可以做到客觀的。[10]
Remove ads
威廉姆斯對於作為一種結果主義理論的功利主義持有完全的批評態度。功利主義的主要觀點是認為所有的行為都應該增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他有一個知名的論據用來批評功利主義觀點,其中故事的主人公是個名為吉姆(Jim)的植物學家。吉姆到一南美洲國家作研究,而這個國家的統治者是一位殘暴的獨裁者。有一天,吉姆發現他在小城鎮中央廣場上遇到了20位被隨機抓來的印第安人,他們都被作為反叛者綁了起來。那位抓捕印第安人的隊長對吉姆說,如果他殺了其中的一人,那其餘的人就會因他是客人而被釋放。但如果他不這樣做的話,那所有的這些印第安人都將被處死。[13]
對於大多數功利主義理論,這種情況下並不存在道德兩難,所有事情都是按結果來判斷的。按照簡單的情境功利主義來看,吉姆應該殺掉其中的一個人。對此威廉姆斯指出,「一個人被我殺死」和「一個人因為我的緣故而被殺死」兩者在道德上有着重要的差別。功利主義者沒有看到這其間重要的差別,把人變成了為達到某一結果的一種工具,而忽視了人是道德行為者與決定者的身份。他認為,道德決定必須保持我們的心理身份和完整性。[13]
他主張,我們實際上並不按行為的後果來評價行為。為了解決倫敦的停車問題,功利主義者會贊成向非法停車者威脅開槍的行為。只有一小部分人因此而被擊斃,非法停車才會停止,於是按功利主義計算幸福的方法就會使開槍的行為正義化。威廉姆斯認為,任何以結果為依據的理論都應該立即被丟棄,無論那種因結果而正義化行為的辯論看起來有多麼合理。作為挽救功利主義的規則功利主義提出,並非是行為、而是規則能夠達到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但問題是,對於停車的例子而言,如果規則是「任何人都可能會因為一個不當停車的行為而被槍擊」,功利主義者便會認為這樣會產生巨大的不幸。對威廉姆斯來說,這恰恰證明了他的觀點。他認為我們不需要去計算為何威脅槍擊是錯誤的,而是應該反對任何涉及到計算的體系。事實上,我們應反對任何把道德判斷轉化為某些算法的體系,因為任何的體系化或還原論都不可避免地扭曲其原本的複雜性。[14][15]

功利主義的一個主要反對者是18世紀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的道德哲學。威廉姆斯從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作品都在對功利主義和康德主義這兩大理論進行批判。馬莎·努斯鮑姆曾寫到,他的著作「譴責在兩個重要理論庇護下英國道德哲學所走的那種瑣碎和逃避的道路」。
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學原理》(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提出了一種他稱之為定言命令的道德體系,其中提到「要只按照你同時認為也能成為普遍規律的準則去行動」。康德認為這是一種對一切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事物都有效的法則。威廉姆斯則在他的論文《人、人格與道德》(Persons, Character and Morality)中反對這種定言命令的說法。他指出道德並不應該要求我們變得無私,就像我們並非我們尋找的自我一樣。他認為我們不應該用一個不偏不倚的觀點來看世界。我們的價值、承諾與欲望都會影響我們看待世界以及我們行為的方式,它們也確實應該是這樣多元化的,否則我們便失去了我們的個性、乃至人性。
Remove ads
威廉姆斯堅持道德是關乎人以及人的真實生活的,因而理性利己主義甚至是自私都並不是與道德行為相悖的。這便是他的「行為的內在理由」學說,也即「內在理由與外在理由」爭論的一部分。[16]
哲學家們嘗試去說明道德規範中有「外在理由」能導致道德行為的履行,也就是說人們能夠出於他們內在心智狀態之外的理由去行動。而威廉姆斯則認為這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某一東西是「行為的理由」,那它一定有某種「吸引力」才能使人們去行動。但是,一種完全外在於我們的東西——例如命題:「X是好的」——怎麼能夠對我們有「吸引力」呢?有什麼機制能使外在於我們的東西能致使我們去行動呢?[16]
威廉姆斯認為這是不可能的。認知並沒有吸引力。他寫道,知道一件事和感受一件事是不同的,人們開始行為前必須要有內在的感受才行。他提出行動的唯一合理性就是內在理由的合理性,無論這種內在理由是撫育、同儕壓力或是其他的欲求。[16]
在其最後的著作《真理與真誠》(Truth And Truthfulness: An Essay In Genealogy,2002年)中,威廉姆斯提出了他認為的真理的兩個基本價值:準確(accuracy)和誠實(sincerity),並以此來填補對真理的需求同虛無主義之間的深淵。其中他對尼采的繼承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將系譜學作為一種解釋和批評的工具。儘管這一著作部分的目的是為了攻擊那些否定真理價值的論述,但書中還提醒到,簡單地作這樣的理解便會錯失這本書想要表達的其他意思。肯內斯·貝克(Kenneth Baker)寫道,這本書是「威廉姆斯對於許多知識分子丟棄真理概念的道德代價的思考」。[9]《衛報》則在威廉姆斯的訃告中寫道,這本書是對那些「嘲笑任何真理假設、認為其可笑幼稚、並認為真理無可避免地會被權力、階級偏見及意識形態所改變」的人的一種挑戰。[10]
威廉姆斯還有一些論文、文章和演講手稿集在其死後才出版,包括談論政治哲學的《一開始就是行為》(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Deed: Realism and Moralism in Political Argument,2005年)、討論哲學與歷史學邊界的論文集《對過去的感覺》(The Sense of the Pas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2006年)、談論形而上學、認識論與倫理學的《作為一門人文科學領域的哲學》(Philosophy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2006年)以及《論歌劇》(On Opera,2006年)。[17][18]
威廉姆斯並沒有提出任何系統性的哲學理論,實際上,他對於任何這種企圖都抱有懷疑。阿蘭·托馬斯(Alan Thomas)寫道,威廉姆斯對於倫理學的貢獻是完全的懷疑主義,在《倫理學和哲學的邊界》(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1985年)和《羞恥與必然性》(Shame and Necessity,1993年)中他明確指出他懷疑為道德哲學建立一個基礎的可能性,並說道德理論永遠無法反映生活的複雜性,尤其是現代社會本質上的多元化。[19]喬那桑·里爾(Jonathan Lear)則寫道,威廉姆斯想要把人作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來理解,[20]道德反省最初的基礎必須是個人的觀點,即行為的內在理由。威廉姆斯認為,想要超越個人的觀點,只能是自欺欺人。[17]
現世人文主義的傳統並不訴諸於一種外在的來自上帝的道德權威,他以此抨擊了傳統道德的基礎,即儘管某人不想做善事他有時也會做成善事、同時他沒能做成時也應該被指責。蒂莫西·查普爾(Timothy Chappell)寫道,如果沒有行動的外在理由,就沒有相同的道德理由集合能夠平等地適用於所有的行為者,因為每一個行為者的理由都與其獨特的生活與內在理由相關。[15]萬一某人沒有任何的內在理由去做其他人看來是正確的事,他就不應該受到指責,因為內在理由是唯一的理由,就如威廉姆斯所說的「指責是將一個沒有理由去做正確事的人當作有理由的人來對待。」[21]
查普爾認為,威廉姆斯著作的基本主旨是,你應該學會做你自己、做到真實和誠實,而非去遵守來自外部的道德體系。[15]「如果說我的著作中有一個主題的話,那就是真實性和自我表現,」威廉姆斯於2002年說,「你應該面對真正意義上你內心的感受,並將它們表達出來……也就是清楚地說明內心必然的想法」。[6]他使得道德哲學離開了康德「我的責任是什麼」的問題,而回到了對古希臘人「我們應該怎樣生活」這一問題的思考。[5]
出版物
|
|
註釋
參考資料
延伸閱讀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Remove a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