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问题
时间线
聊天
视角
社会性别
社會科學概念,包含物理、心理及行為特徵等,以陽剛特質和陰柔特質作為區別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Remove ads
社会性别(英语:Gender)[注 1],或性别身份包括作为男人、女人或其他性别认同的社会、心理、文化和行为层面。[2][3]根据情境,这可能包括基于性别的社会结构(性别角色)以及性别表现。[4][5][6]大多数文化采用性别二元制,将性别划分为两个类别,人们被视为属于其中一类(男孩/男性和女孩/女性);[7][8][9]那些不属于这些群体的人可能被归为非二元性别的范畴。部分社会接纳男女以外的社会性别,比如在南亚地区中,海吉拉常被视作第三性别(或第四性别等等)。大多学者认同社会性别是社会组织的核心。[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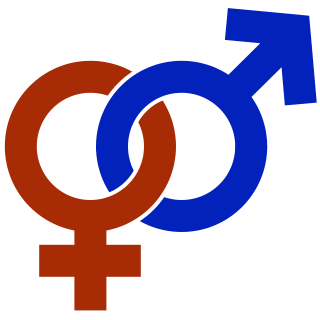

在英语中“Gender”(社会性别)一词也常被用作“sex”(生理性别)的同义词,而这两种用法之间的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11][12][13]在20世纪中叶,现代英语中开始出现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术语区分(即性别之分),这一区分起初发展于心理学、社会学、性学和女性主义等学术领域。[14][15]在20世纪中叶之前,英语圈主要以社会性别的英语“gender”代指文法上的分类。[2][4]在西方,到了1970年代,女性主义理论采纳了生理性别与社会建构的性别之间区分的概念。当今,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家、[16][17][18]行为科学家与生物学家、[19]许多法律系统和政府机构、[20]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等跨政府机构[21]都对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进行区分。
社会科学中有一个分支专门研究社会性别,即性别研究。其他科学领域,例如心理学、社会学、性学和神经科学,也对社会性别这一主题表现出兴趣。社会科学有时将性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而性别研究尤其如此;自然科学的研究则探讨人类的性别差异是否影响人类中社会性别的形成。这两种研究共同促进了对生物差异在性别认同和性别化行为形成中影响程度的讨论。生物—心理—社会模型(biopsychosocial approaches)将性别视为包含生物、心理以及社会或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22][23]
Remove ads
词源及应用
现代英语“gender”的前身为中古英语“gendre”。后者借用了盎格鲁-诺曼语和中古法语的同样字词。而“gendre”则来自拉丁语的“genus” ——两者皆指“类型”。它最终可追溯到原始印欧语的词根“*ǵénh₁-”,意即“产生”和“孕育”[24]。它跟“kin”、“kind” 、“king”等同根。此外亦与其他印欧语系的部分词汇同源[25],像是现代法语的“genre”。它跟希腊语词根“gen-”有一定关系,后者成为了英语“gene”、“genesis”、“oxygen”的一部分。1882年的《牛津英语词源词典》把“gender”定义为“种类、品种、性别”,指其就像“genere natus”(出生)般,一样源自拉丁语中的离格“genus”[26]。
社会性别是近代的概念[27]。在20世纪中期,人文社会科学界才开始着力探讨之[27]。现时意指社会性别的英语“gender”在此之前一直只跟文法有关[28]。
英语圈在用字上尝试区分生物性别和性别角色之前,“gender”一般只用在文法分类上[29][30]。比如一本有关婚姻家庭的书籍虽列出12,000多条1900年至1964年出版的参考资料,但当中没有出现“gender”一词[29]。研究者在分析3000万篇1945年至2001年出版的学术文章标题后,得出结论: 早期的文章很少应用到“gender”,其应用多跟文法分类有关。到了1970年代,女性主义学者开始把生物性别和社会对性别的建构分开,致使人文社科界使用“gender”的次数远多于“sex”[30]。
到了1980年代至1990年代,在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学者使用“gender”的次数出现较大幅的增长,在社会科学界中甚至抛弃“sex”一词。但在实际应用上,部分人会把之当作“sex”的同义词,违背原意。戴维·A·黑格提到:“在生物学界,部分科学家以‘gender’替代‘sex’是为了表达对女性主义理想的认同。其他的可能认为此一用法较有学术风格;或能以之减少歧义,避免跟交配混淆”[30]。1993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为了减少歧意,决定以“gender”取代“sex”[31]。2011年,FDA决定在生物分类上改用后者,前者则改以形容“人们对自身是男或女的展示,以及社会制度对此的反应”[32]。
2006年,梅雷迪斯·伦德(Meredith Render)在回顾多宗有关歧视的判决时写道:“自1964年民权法案生效以来,性/别的观念起了不少变化,令法案中性别歧视的涵意也随之变迁”[33]:135。朱莉·格林伯格(Julie Greenberg)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倡把“sex”的法律定义延伸,令之更为强调“自我性别认同”。他写道:“大多法律条文都采用‘sex’一词,但法院以及立法和行政机关往往在解释法规时以‘gender’取代之”[34]:270, 274。在J.E.B. v. Alabama ex rel. T.B.案中,美国最高法院为“平等保护条款是否禁止建基于社会性别的歧视”颁下判决,大多数意见认为需承认“我国在性别歧视上有着一段难堪的过去......提醒我们需严格考虑所有建基于社会性别的分类是否合理......当各州行为者只因对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而要求某人无因回避时,他们就在认同和加深男女相对能力不同的偏见”[35]。
1945年,麦迪逊·本特利把社会性别定义为“社会对生物性别的观察”[36][37]。4年后,西蒙·德·波娃在《第二性》中开始套用该一区别,使得此一概念正式步入女性主义理论[38][39]。不过萨拉·海纳玛表示此一演绎有一定争议[40]。
性别角色的概念由性学家约翰·曼尼所创[41][42]。他在1955年的一篇文章中把它定义为:“人们为表达自己是男是女的所说所行”[43]。最迟在1945年,学者开始以社会性别来表达性别角色[44]。
经历性别(experienced gender)是一个罕见的术语[45],指的是个人实际感知和经历到的性别。它考虑了个体对自己的性别身份和经验的认知。社会性别和虽然相关,但并非完全等同。社会性别指的是社会对个体所赋予的性别身份及社会对此的性别角色的期待,而经历性别更强调个体在生活中所感知和体验到的与性别相关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会互动、文化认同和自我身份感受等。社会性别强调了社会角色和认同,而经历性别更关注个体在不同情境下对性别的感知和体验。
性别认同与性别角色

性别认同指人们对特定性别和性别角色之认可。在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出现之前,女性一直靠着身体特征来定义,之后一些女性主义者开始挑战这一理解[46]。
女性主义者会挑战有关性别角色和生物性别的主流意识形态。朱迪斯·巴特勒认为“生为女性”的概念具有较大挑战空间,因为它除了是一门社会分类之外,还是一种自我认知和文化建构的主观认同[47]。社会认同是一种建基于社会分类的共同认知,能够让成员创造出共同文化 [48]。社会认同理论认为[49]。社群之间的互动和共同经历会为人提供相当一部分的自我概念,塑造人们如何举止的规范[50]。
在社会角色上把人以男女二分会让部分人认为自身只属于当中一种角色,并按其规范行事。但社会角色事实上是一门光谱,人们可处于当中的任何一点[51]。世界各地都会以男女在的生物差别为由,创造出一套界定他们该如何举止的社会期望。并在权力、权利、资源分配等事宜上作出差别待遇[52]。大多社会会优待男性,令它们出现性别不平等的现象[53]。很多社会皆为性别创造出一套规范和信念,不过性别角色却没有普世划一的定义[54]。男女在社会上的角色和彼此之间如何互动皆受文化规范影响,令一套性别系统得以诞生。它是很多社会格局的基础,令它们隔离性别和偏好于男性气质[53]。
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人是性的主体,但却受制于权力影响,而它最终可归因于“各种权力策略”[55]。权力决定了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并令人们受到标签。比如女性在不少社会上被视为情绪化和柔弱的,没能力作出跟男性一样的行为。朱迪斯·巴特勒表示,社会在把自身视为女性的同时,也把一套行为举止规范施加在自身身上,因此性别更像是个动词。他表示“因为社会把性别视作政治的一部分,并对之作出规限,所以它不许我自由建构自身的性别......”[47]。不过也有批评指其行文加强了传统的性别二分法[56]。
Remove ads
性别理论家凯特·博恩斯坦表示,社会性别存有一定的模糊地带,并具流动空间[57]。至少有两套不同但又有共通之处的理论定义了何谓社会性别[58][59]:
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社会性别为“社会建构的男女特质”[60]。根据该一定义,社会性别是社会规范加诸于人们身上的信念和态度,个人对此的看法相对而言较不重要[61]。
社会为人指定社会性别时,会先考虑人们与生俱来的外表及生理特质,然后按此一特质分配社会认为合适的行为举止。因此社会性别指的是特定社会文化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建构。尽管生物性别是一门可以得到人们认知的事实,但性别角色会因文化而异[62],且受到照顾者、学校教育、媒体的影响。因此,社会性别自幼开始便开始习得——例如为婴儿挑选的玩具和衣服都是学习有关规范的途径。不过,人们的社会性别不一定跟其出生时指定的性别相符,其还会受学习行为等因素影响[63]。
Remove ads

性学家约翰·曼尼于1955年创造了性别角色一词。他把性别角色定义为可能会表露某人为男孩/男性或女孩/女性的行为及反应[64]。性别角色的要素包括衣装、说话方式、行动、职业。一些女性主义哲学家不认同社会性别是一门分类,认为它不是“表象背后的原因”,反之却是“一种宏大编排,作用于自身跟他者之间的微妙中介之上”[65]。
大多社会在过去都只把人按生物特征分为两种性别角色[9][66][67]。它们会根据婴儿的性器官,为之分配社会性别[62]。
不过仍有一些社会会承认有些人处于男性—女性气质光谱的中间。例如夏威夷人会承认他们的社会有人是处于“男女之间”,他们称这一群体为māhū[68][69],在奥吉布瓦语中,“ikwekaazo”或“ininiikaazo”指的都是选择以另一性别角色过活的人[70]。性别社会学研究者会把上述情况称为第三性别。符合上述身份的当代美国原住民和加拿大原住民可能也认为自己是属于双灵圈子[71]。不过,这类概括式语言可能不为该些社群大多成员所认同[72]。
能够归作第三性别的还有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海吉拉,以及墨西哥瓦哈卡州的muxe[73][74][75]。苏拉威西岛和印度尼西亚的布吉人在传统上有着与上述分类不同的系统[76]。
除了第三性别外,现在许多文化皆接受了各种的非二元性别。非二元性别者的性别认同不全然偏向男或女的任何一方。他们可能会自认为在性别认同上部分重叠、拥有多于一种性别、没有性别、性别认同处于流动状态、第三性别等等。主流西方社会在较后期才承认非二元性别[77],而后者拥有较高风险面对侵犯、骚扰、歧视等问题[78]。
早期的性别认同研究一般只会假定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为线性的连续体。不过社会对男女的定型会随着时间改变,因此此一模型的效度备受质疑。于是便有人提出以两维作基本概念的性别认同模型,当中男性气质及女性气质成会分成两个正交的维度去量度。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同时存在。此一概念于当下已成了广为接受的标准[79]。
贝姆性别角色量表(BSRI)及个人属性问卷(PAQ)是性别认同研究较常应用的测量工具,两者皆考虑到男性气质及女性气质不只是处于单一维度。按照该些测量工具的结果,可以把人分为传统性别型(主要认同自己拥有男性气质的男性或主要认同自己拥有女性气质的女性)、反传统性别型(主要认同自己拥有女性气质的男性、主要认同自己拥有男性气质的女性)、双性型(两种气质皆有一定程度认同的人)、未定型(两种气质皆欠缺认同)[79]。特温格在1997年表示,男性一般比起女性拥有更多的男性气质,女性则一般拥有较多的女性气质,但它们与生物性别的关系相对以前不那么强烈[80]。
Remove ads
生物学家兼女性主义学者安妮·福斯托-斯特林反对有关“生物本质论对社会决定论”的论述,并提倡应更深入地分析生物体与社会环境之间会怎样产生影响某人能力的互动[81]。哲学家兼女性主义者西蒙·德·波娃把存在主义应用于女性的生活经历中:“我们并非生来为女人,我们是成为了女人”[82]。尽管这在语境上只是哲学方面的修辞手法,但其同样适用于生物学上的语境——一名少女必须经历完一整段青春期,才可成为女人;而在社会学的语境上,成熟并非一种本能现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习得的[83]。
自1970年代起,女性主义理论在探讨性别议题时的用字便出现了争议。1974年出版的《Masculine/Feminine or Human》中,其作者使用了“内在的性别”(innate gender)和“习得的性别角色”(learned sex role)这两个词[84],然而到了1978年的版本中,“sex”和“gender”的用法却倒过来了[85]。到了1980年,大部分女性主义的文章都会将“gender”仅仅用作社会文化上性别的自我认同,以便与生物上的性别(sex)区分开来。
在性别研究当中,社会性别是在指社会及文化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建构。在此一语境底下,社会性别明确地排除了生物上的差异,反之却专注于文化差异[86]。此一情况在其他领域当中亦有出现,例如1950年代的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家雅各·拉冈的理论、法国精神分析学家茱莉亚·克莉斯蒂娃等人的研究、像朱迪斯·巴特勒般的美国女性主义者。巴特勒的追随者倾向认为性别角色是一种行为实践,亦即其是表演性的[87]。
查尔斯·赫斯特称,一些人相信性别会“......自动决定某人的性别气质、角色(社会上的),以及性取向(对特定性别的性偏好及行为)”[88]。性别社会学家则相信人们所展现的社会性别有其文化根源及习惯。比如迈克尔·斯瓦洛相信,人们须透过学习,才能懂得如何作出与其指定性别相符的行为,及从互动中了解到怎样的举止才符合社会对男性或女性气质的期望。斯瓦洛评论道,人类“是许多人接受相近思想,并就此采取行动之结果”[89]。从衣装到个人发型,从关系选择到职业选择,人们无不受到此一过程的影响。斯瓦洛认为,这些类型的区分是很重要的,因为社会一看到人,就想把他们识别和分门别类。他们需要将人们放入不同的类别,以让人能够知道应该如何看待某个特定人物。
赫斯特认为,在人们需要明确表达社会性别的社会当中,相关文化规范一旦被打破,那么当事人就通常需面临某些特定的后果。当中很多是扎根于性取向歧视之上。他表示在某些社会当中,同性恋者常因为社会偏见,而在司法系统中面临歧视[90][91][92]。赫斯特曾就司法系统对于打破性别规范者的歧视情况进行过描述,他表示:“法院经常把性别、社会性别、性取向混为一谈,使得它不仅否定男同性恋者及女同性恋者的权利,而且连带不符合传统性别期望者的权利也一并否定”[88]。
基进女性主义者安德里亚·德沃金在描述她的信念时表示,她会“致力摧毁男性的支配地位及社会性别本身”[93]。
政治科学家玛丽·霍克斯沃斯发表了有关社会性别和女性主义理论的论述,她指出社会性别一词的涵意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或以后,于女性主义学术界当中出现了转变,并且以明显不同的方式应用在学术研究中。她称,当包括桑德拉·哈定及琼·瓦拉赫·斯科特在内的几名女性主义学者,开始认为社会性别“为一门分析性分类,包含人类的所思所想所行”时,它的涵意便出现了变化。政治科学领域的女性主义学者此时开始把社会性别视为分析性分类,其中强调了“被主流论述所忽视的社会和政治关系”。不过霍克斯沃斯同时称:“女性主义政治科学并没有成为学科内的主流范式”[94]。
美国政治科学家卡伦·贝克维思同样对于政治科学之内的性别概念有所论及,她认为的确存在着一种有关“社会性别的共同语言”,且其必须加以明确阐述,以使之更为扎根于政治科学之内。贝克维思描述了政治科学家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可以怎样运用“社会性别”一词,指应视其为“一门分类,或一个过程”。若将社会性别视为一门分类,那么便可使政治科学家在某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中,“界定被视为展露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的行为、行动、态度和偏好”。它还可用于论证社会性别差异会怎样“制约或促进政治”行为者。若在政治科学研究中把它视作一个过程,那么便有两个不同面向:一是确定“结构和政策对男女的不同影响”,二是男女政治行为者如何“积极努力地产生有利的性别结果”[95]。
对于性别研究此一领域,雅克塔·纽曼称尽管性别是生物决定的,但人们如何表达自身的社会性别却不受制于生物状态。性别化(Gendering)是一个建基于文化之上的过程,尽管对于男女的文化期望往往与他们的生物状态有直接关系。纽曼认为,正因为如此,很多人把性别视作压迫的原因,而忽视了其他问题,比如种族、能力、贫穷。为了改善这种情况,目前的性别研究课程会把更多因素纳入范围,研究这些因素在决定人们如何生活时会怎样互相影响。她还指出,其他非西方文化对社会性别和性别角色的看法不一定与西方相同[96]。纽曼还质疑了“平等”一词的含义;“平等”一般为女性主义的目标。她认为“平等”一词本身就是有问题,因为它所指的可以有不同,例如其可指待遇相同,但亦可指按著性别而出现不同的对待,抑或公平地对待任何一种性别者。纽曼认为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平等一词没有统一的定义,而定义精确在公共政策等领域可能是非常重要的[97]。
Remove ads
总结
视角

社会学家通常认为社会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此外不少研究者只把性别视为生物的,并否定其有任何的社会或文化建构成分在内。此一情况在女性主义者当中尤其普遍。比方说,性学家约翰·曼尼把生物性别(biological sex)及性别角色(gender as a role)区分开来使用[64];社会学及社会政策教授安·奥克利同样称:“人们必须承认性别的恒定性,但同时必须承认社会性别的可变性”[98]。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性别是指定义某人是男是女的生物生理特征”,而社会性别则“指社会构建的,并被特定社会认为适合于男性和女性的角色、行为、活动和特性”[99]。在上述语境下,性别是指生物学(自然科学)研究上的分类,而社会性别则是指人文社科的研究重心之一。女性主义生物学家林达·伯克认为“生物学上的事并非可以出现转变的”[100],因此该些学者视性别为恒定的,而社会性别则会随社会结构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性别同是社会建构下的产物。例如性别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其表示:“也许这种被称为‘性别’的建构跟社会性别一样,都是文化建构的;事实上,社会性别可能本来就已经存在。由此推导下去,性别跟社会性别基本就没有任何区别了”[101]。
其继称:
如果性别本身就是一个以社会性别为中心的分类,那么继续‘把社会性别定义为对性别的文化诠释’这件事本身就没有意义可言。社会性别不应仅仅被视为建基于指定性别(一种法律概念)的文化刻画,而是须视之为生产机器,而性别本身就是因这种机器而确立。……在前语言上,这里所指的性别生产应被理解为由社会性别所指定的文化建构机器的效果。[102]
巴特勒认为:“身体只是在某些规管图式高度社会性别化的生产性制约当中存在着、忍受着、生活着”[103],而性别“不再只是有关身体的......它是一种支配身体物质化的文化规范”[104]。
妇女研究及历史系教授琳达·尼科尔森在回顾历史时指出,在历史上绝少有人以“性别有异”的方式理解人体。她继指西方在18世纪之前,一直认为两性性器官实际上是一样的。该时西方主要把视为女性性器官不完整的男性性器官,而二者之间的区别只是程度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相信此事为渐变的,抑或具有光谱性质[105]。此一说法已受到像海伦·金、琼·卡登、迈克尔·斯托尔伯格般的学者的批评[106][107][108]。
生物学系兼性别研究系教授安妮·福斯托-斯特林则从双性儿童的实证研究出发,介绍了医生会如何解决双性人问题。她以一个双性人的出生为例展开论证,认为“我们对性别差异的概念塑造了,甚至反映了我们建构社会制度和政体的方式;它们也塑造和反映了我们对身体的理解”[109]。然后她引用了约翰·曼尼等人对双性人的研究,以此引证性别假设是如何影响性科学研究:“他们从来没有质疑过只有两种性别的基本假设,因为他们研究双性人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更多何谓‘正常’发展”[110]。 她还提到了医师对双性人的亲属解释相关情况时所用到的语言。她称,由于医师还是认为双性的新生儿实际上要不是男的,就是女的,故此会告诉父母需要花多一点时间去辨其雌雄。 也就是说,医师的行为是由认为只有两种性别的文化假设所塑造的。最后她提到了不同地区的医护对于双性新生儿的处理手段存有差异,这很好地说明了性别本身也会被社会构建[111]。她在《身体的性别化:性别政治和性的构建》一著中提到了以下例子:
最近,来自沙特阿拉伯的一组医师团队报告了几例患有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症的XX双性新生儿案例——该症为遗传性障碍,会影响促进类固醇激素生产的酶……在欧美地区,这样的孩子由于有机会于日后生儿育女,故此一般会被当作女孩抚养。受过这种欧洲传统培训的沙特医师向新生儿的父母提出了上述建议,但其中一些表明不会接受,即他们不愿把当初视为儿子的婴儿当作女儿般抚养。他们也不接受为之进行女性化手术……这基本上是当地社区态度的体现……他们更喜欢男性后代。[112]
故此现有证据表明,文化的确在指定性别当中扮演了一定角色,对于双性孩童的情况而言更是如此[111]。
在《青少年的性别角色认同与心理健康:重新审视性别强化》一文中,希瑟·普里斯、萨拉·林德伯格、珍妮特·史布利·海德等人探讨了性别认同在青少年时期会否出现偏离。研究者的研究建基于希尔和林奇在性别强化假说中提到的观点,即来自父母的信号和信息会决定并影响孩子的性别角色认同。这一假说认为,父母会影响孩子的性别角色认同,而与其中任何一方的互动多寡则为性别强化的自变项。普里斯等人的研究并不支持希尔和林奇所提出的假说——“随着青少年经历这些和其他社会化影响,他们在性别角色认同、性别态度及行为上会变得更加刻板”[113]。不过他们亦表示,也许希尔和林奇的假说在过往是正确的,但现在却因为青少年群体在性别角色认同方面的变化,而变成错误的。
《解读性别系统:性别信念和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的著者塞西莉亚·里奇韦及雪莱·科雷尔认为,社会性别的范围远超于角色及认同,直指它为透过“社会关系脉络”制度化的事物。里奇韦及雪莱把“社会关系脉络”定义为“个体将自身与他者的关系确定下来,以采取行动的任何情境”[114]。他们还指出,除了社会关系脉络,文化信念在性别制度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他们认为,人们每天都在被迫以跟社会性别有关的态度举止来承认他人,与之交往。每天人们都在遵守社会既定一套的霸权式标准信念的前提下,互相交流,其中包括有关性别角色的一套信念。他们指出,社会的霸权式标准信念设下了一系列规则,而这些规则又为“社会关系脉络”的促成背景。里奇韦和科雷尔随后一转议题,探讨性别分类,把它定义为“我们为某人贴上男性或女性标签的社会认知过程”[114]。
生物学因子与视角
在大多情况下,男性和女性的所作所为十分类似,当中只有很少的性别差异,不过产前及童年所接触的雄激素会对性别化行为构成一定影响。该些行为包括性别规范性游戏、性别的自我认同、从事侵略性行为的取向[115]。大多数雄性哺乳类动物在进行游戏行为时,会因睾酮的影响,而表现得较为粗暴。这点在人类当中也不为例外。同样,睾酮的水平可能会影响到性本身——非异性恋者倾向在童年时期作出并非性别典型的行为[116]。
在20世纪末,生物学上的性别开始成为众多研究的探讨重心。早年不少研究聚焦探讨性别认同障碍,亦即现在的性别不安。约翰·曼尼就著上述或相关领域的研究,为这一议题下了个总结:
“性别角色”一词可追溯至1955年的一篇印刷文章。“性别认同”一词则可追溯至1966年11月21日的一篇新闻稿,当中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宣布,他们开办了一间专为变性者而设的新诊所。这一用语在经过各大传媒传播后,便广为世界认知,并被翻译成各国方言。在理论基础上,社会性别和性别认同的定义存有不同。在大众化和科学化的用法当中,性别是指你在生物学上是什么;社会性别指你在社会上成为了什么;性别认同指你对自己是男是女的意识或信念;性别角色则指文化对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性别认同障碍的决定成因可分为几个大类,包括基因、产前激素、产后社会、青春期后激素。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提出一个全面而又详细的因果关系理论。脑部的性别编码是双相的。患有性别认同障碍的人的先天外生殖器性别,与脑部的性别编码不一致[117]。
尽管众多研究证明了生物(遗传及激素)到行为的因果关系,但曼尼还是小心地指出,在性与性别问题上,生物到行为的因果链仍然未建立好。比如说尽管大多科学家会承认同性恋基因的确有可能存在,但迄今尚没有实证证明此类基因是存在的[118]。
目前已有有关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症女性患者的研究。此症会使患者身体产生过量的雄激素。该些女性的外表跟其他女性差不多(但她们一般需要进行生殖器矫正手术)。不过即使自幼便一直摄入激素平衡药物,她们还是会对传统上与男性有关的行为展露出较大兴趣。心理学教授兼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症研究者谢里·贝伦鲍姆博士认为,此一差异可由以下事实解释:她们于宫内长期接触较高水平的男性性激素[119]。
以下性别分类法根据现有的医学研究列出。它按着人类生命周期,把生物性别到社会性别顺序列出。周期的早期阶段多为生物性的,后期则更为社会性。
- 染色体:46条染色体,性染色体为XX (基因上的女性);46条染色体,性染色体为XY(基因上的男性);45条染色体,性染色体为X (特纳氏综合症);47条染色体,性染色体为XXY(克氏综合症);47条染色体,性染色体为XYY (XYY-三体);47条染色体,性染色体为XXX (三染色体X综合症);48条染色体,性染色体为XXYY(XXYY综合症);46条染色体,性染色体为XX/XY镶嵌;其他镶嵌现象
- 生殖腺:睾丸;卵巢;同时具有卵巢和睾丸组织(真性阴阳人)、具有卵精巢,以及其他性腺发育不全表现;
- 激素:雄激素(包括睾酮、双氢睾酮)、雌激素(包括雌二醇、雌三醇)、抗雄激素、孕激素等等;
- 第一性征:生殖器[120];
- 第二性征:第一性征以外的二形身体特征(比如体毛、乳房发育);因性激素而起的脑部变化[121]。
- 性别认同:某人对自己是男是女,还是非常规性别者的感受;
- 性别表现:表达自身性别认同或性别角色的表现及行为。

大多人类拥有23对(46条)染色体。当中第23对为性染色体[122],用以决定影响个体最终发育成雌性(XX)还是雄性(XY)[123]。卵子所携带的一般是X染色体;而精子则有一半机会携带Y染色体,另有一半携带X染色体[124],故此后代的性别将由男性方的精子决定[125]。不过这也有可能产生性染色体不属上述两者的后代[125]。
X或Y染色体特有的基因即为性连锁基因[126]。最常发生红绿色盲的相关隐性遗传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男性只有一条X染色体,而女性则有两条X染色体,缺失的基因可以由另一条补足,故此男性比女性容易有色盲[127]。
人类的XY系统并非世上唯一的性别决定系统。鸟类的情况跟人类相反,牠们以ZW系统决定性别—— ZZ为雄性,ZW为雌性[128]。人类尚不了解是否全部鸟类都是由雌性或雄性方的配子决定性别。已知有几种蝴蝶的后代性别由雌性方的配子决定[129]。

“现有广泛证据证明男性的大脑比起女性大约8-10%(Filipek et al., 1994; Nopoulos et al., 2000; Passe et al., 1997a,b; Rabinowicz et al., 1999; Witelson et al., 1995)”[131][132]。但较与脑部功能有关的是其结构及神经连接方式。新墨西哥大学及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的研究者以脑造影的方式研究了男和女的脑部,发现男性比起女性拥有更多跟一般智力有关的灰质,女性则比起男性拥有更多跟智力有关的白质—— 男性的灰质:白质比比起女性高4%[131]。
灰质是负责进行资讯处理的组织,白质则负责协调各个处理中心。它们亦量度了其他方面的差异,不过却没有仔细写出相关结果[133]。这些差异大多为激素所致的,且最终可把原因追溯至Y染色体和性分化上。但也有基因活动直接导致的差异。
[我们]透过定量实时聚合酶链式反应观察到,脑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存有性别二态性。当中女性的PCDH11X转录水平高出了2倍。我们把此一发现跟人脑的性别二态性性状划上联系。有趣的是,PCDH11X/Y基因对是智人独有的。它们自从人类-黑猩猩谱系分成一派后,性连锁基因便转座到Y染色体上。
——[134]

此外也有证据证明,脑部的处理过程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行为及思想学习皆会编码脑部的处理过程。在对几个个案的简单研究当中,发现相关脑部编码过程也会出现男女不一致的情况,但在某些方面是相同的[135]。例如即使男女两方都在学习和使用语言,但在生物化学上,两者对语言的处理方式会出现差异。女性和男性在使用语言方面的差异,很可能反映了他们在生物上的偏好和天赋,以及学习模式。
睾酮会影响身体众多器官,包括位于脑部性别差异神经核的性别二型神经元,以及位于脊髓的欧氏核,使其运作模式更为男性化[136][137][138]。
性别研究
性别研究是一门把社会性别、性别认同、性别表述视作中心去分析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它包含了妇女研究(研究女性、女性气质、她们的性别角色、性别政治、女性主义)、男性研究(研究男性、男性气质、他们的性别角色、性别政治)、LGBT研究这几个范畴[139]。有时提供相关课程的院校会把它连同性学课程一起提供。该些学术领域会从文学、语言、历史、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电影研究、媒体研究、人类发展、法律、医学等角度,去研究性与性别[140]。它还会对人种、族群、地理位置、国籍、身心障碍等议题进行分析[141][142]。
心理学与社会学

当代社会化理论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人刚出生时,只有生物性别,没有社会性别[来源请求]。随着孩子的成长,“......社会提供了一连串[在规范上]适合某一性别的行为指示、模板、模式”[143],把孩子社会化成一种特定的社会性别[来源请求]。社会上存有极大的诱因去促使其顺从社会化过程——社会性别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某人在教育、工作、家庭、性、生育等层面上所获得的机会[144],并会影响文化及知识的形成[145]。从这个角度看,不好好履行相关社会规范的成年人会被社会视为越轨或社会化不当[146]。
也有理论认为,社会性别被构建社会的社会组织分割成二元;同时社会组织又不断地发明和再生产社会性别的文化形象。琼·阿克认为,性别化发生在至少五个互相影响的社会进程当中[147]:
- 性别分工的建构,例如在劳动、权力、家庭、国家层面的性别分工,以至容许的行为及出现的地点
- 符号及形象的建构,包括语言、意识形态、衣装、媒体。它们会解释、表达和加强(有时减弱)性别分工
- 任何处于支配与服从关系的人的互动。比方说会话理论家研究了在日常交流的过程中,打岔、话轮转换,以及话题设置会怎样重塑性别不平等的现象
- 上述三个过程对个人认同当中的性别部分的影响, 即它们会怎样产生及维持性别化的自我形象
- 社会性别牵涉到基本社会结构的持续塑造和概念化。
若以福柯的观点分析社会性别,它就会被视作社会用于权力分工的工具。性别差异仅仅是一种用于强制性地区分假定男女的社会建构。之后再透过赋予与性别有关的特质,使男性气质可以支配女性气质[148]。“有人认为男女之间的差异比起其他的还要大。这种想法一定是来自于自然以外的......这远超过先天差异本身,具有排他性质的性别认同抑制了先天的相似性”[149]。
性别惯例为“把男女气质简单地归因于生理性别”的主因[150]。社会文化的准则和惯例,以及社会运作的规则,都是社会的产物和构成要素,并决定了分配哪些具体特质至性别上。这些特质又为霸权式性别差异的诞生提供了基础。因此,社会性别可被视作社会规范的获得和内化。人们继而因为接受了社会的性别期望,而被社会化。该些期望可见于家庭、国家和媒体等制度当中。这样的“性别”概念最终被归化为某人的自我意识或身份认同。这在实际上,就是将一个性别化的社会类别强加给一副性的身体[149]。
“人是被性别化(gendered)的,而非性化(sexed)的”这一概念也跟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性理论不谋而合。巴特勒认为,社会性别与某人表达了自己是什么无关,反之却跟其行为有关[151]。由此可见,如果社会性别以不断重复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它实际上就是在社会意识当中,重新塑造了自身,并深深地嵌入之。
社会学和大众对于社会性别的定义存有矛盾之处,且侧重点也会有不同。比方说,社会学会在考虑男性CEO与受雇于他的女性员工之间的(经济/权力)地位差异时应用到社会性别(社会角色:女性与男性),当中不会考虑涉事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然而大众会在考虑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的自我概念和社会观念时应用到社会性别,当中不会考虑涉事人的经济/权力差异。因此在社会性别的定义和应用上,传统女性主义社会学与当代同性恋社会学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152]。
社会性别与社会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把科学描述成一门具有男性气质的领域。不少想投入科学领域的女性需面对较大的障碍[153]。即使大学于19世纪开始招收女性,但她们仍被认为只适合某些科学领域,比如家政学、护理学、儿童心理学[154]。女性在科学领域的就业前景并不乐观,上级常把她们安排去从事一些低薪乏味的工作,发展路向同样受限[154]。这往往是由刻板印象造成的:人们常认为女性先天较适合从事一些需要専注力、耐性,和手巧的工作,相比之下需要创造力、领导力、智力的工作则被视为不适合女性从事[154]。虽然有关刻板印象到了现代已渐渐消退,但女性仍很少投身于物理学等著名的 “硬科学”领域,而且在当中晋升至高级职位的可能性往往较低[155]。
女性在贫穷此一议题上较常面临性别不平等的现象。许多女性都需对家中每事负全责,因为所有的家事重担都完全落在她们身上。耕地、磨粮、担水、做饭等等,很多时候都只由她们负责[156]。除此之外,女性很容易因性别歧视,而获得较低的收入;男性则较容易获得较高的收入,而且拥有较多的机会及社会政治资本[157]。世界上大约75%的女性因工作不穏,而无法获得银行贷款[156]。这表示尽管世间女性很多,但只有少数是富人。内娜·斯托伊尔科维奇于《D+C发展与合作》当中指出,许多国家的金融部门常常忽视了女性本身,即使她们在经济上举足轻重[158]。戴安娜·皮尔斯于1978年创造了“贫穷女性化”一词,用以形容女性贫穷率较高的问题[159]。由于在收入分配、财产所有权、信贷和所得收入控制方面长期存有性别不平等的现象,所以女性更容易陷入长期贫困[160]。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常伴有性别偏误,这一现象同样适用于国家层面的资源分配[160]。

性别与发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是一套综合计划,其会向那些社会和经济发展严重受到性别不平等现象影响的国家提供援助。它是一套侧重于女性性别发展的计划,最终目的是透过为女性赋权,来降低男女不平等的程度[161]。
2013年一项有关歧视跨性别者的大规模研究发现,跨性别者比起顺性别者有多4倍机会活在极端贫困(年收入低于1万美元)之中[162][163]。
应用了一般紧张理论的研究表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别差异可使人表露出愤怒的情绪,甚至引发暴力冲突[164]。这些与性别不平等有关的暴力行为可以透过比较暴力与非暴力社区来衡量[164]。当中只要留意自变量(邻里暴力)和因变量(个人暴力),即可以此分析性别角色[165]。一般紧张理论中的“紧张”是指在失去一个正向刺激,或/和增加一个负面刺激时,对涉事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紧张)。其影响可以是向内的(抑郁/内疚),也可以是向外的(愤怒/沮丧),取决于涉事人会怪责的自己还是环境[166]。研究表明不论男女,在面对紧张时都会以愤怒作回应,但愤怒的根源及他们的应对手段会有很大不同[166]。男性较有可能怪责他人,把愤怒外化[164]。女性则一般把自身的愤怒内化,倾向于责怪自己[164]。 女性在愤怒的同时,常夹杂着内疚、恐惧、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165]。女性认为愤怒是失去自身控制的迹象,因此担心这会伤害他人/破坏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光谱的另一端,男性则不太在意会破坏关系,更会利用愤怒肯定自身的男性气质[165]。根据一般紧张理论,男性更有可能因外在化的愤怒而作出攻撃性行为;而女性则会将愤怒指向自己,而非他人[166]。此外情绪亦会受到社会性别的影响。英格拉姆等人(2012)的研究显示,“按照研究对象的假设,人们在对男孩过去的冲突进行描述时,会较描述女性的冲突时多用到愤怒去形容”,不过“人们较多描述女孩在冲突过后的愤怒”。特恩卡在2013年探讨了此一现象的背后原因,但仍然不能找到合理解释[167]。另有研究显示,研究对象对于男性的恐惧表情存有较佳的识别能力。女性对恐惧表情的识别能力也普遍优于男性[168]。
性别是气候变化政策及科学日益关注的一个议题[169]。一般而言,科学界较为关注的是气候变化对于不同性别所产生的不同后果、不平等的气候适应能力,及性别差异如何影响气候变化本身。此外,气候变化与性别问题的交集也带出了复杂的权力关系问题。这些差异大多不是生物因子所致的,反而社会、制度和法律因子于当中较为重要。因此,与其说脆弱性是女性和女孩的内在特征,倒不如说是她们被边缘化后的产物[170]。罗尔[171]指出,虽然联合国承诺会推动性别主流化,但在气候变化政策方面,实际上它并没有真正实现性别平等。而这正好反映在有关气候变化的话语和谈判之中——它们仍为男性主导[172][173][174]。一些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有关气候变化的探讨不仅由男性主导,而且在原则上十分“男性化”,令有关探讨十分专注于技术层面[173]。这种对气候变化的了解,把限制了气候变化政策和科学的主体性或权力关系给隐瞒起来[173],从而导致了图阿纳[173]所指的“认识论不公”。无独有偶,麦格雷戈[172]同样认为,人们透过将气候变化以“硬”的自然科学和自然安全问题包裹起来,来把之困在传统男性气质霸权的领域之中[172][174]。
参见
注解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Remove a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