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函数
量子力学中量子态的数学描述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在量子力学里,量子系统的量子态可以用波函数(英语:Wave function)来描述。薛丁格方程式设定波函数如何随著时间流逝而演化。[注 1]

波函数 是一种复值函数,表示粒子在位置 、时间 的机率幅,它的绝对值平方 是在位置 、时间 找到粒子的机率密度。以另一种角度诠释,波函数是“在某时间、某位置发生相互作用的概率幅”。[1][注 2]
历史


在1920年代与1930年代,理论量子物理学者大致分为两个阵营。第一个阵营的成员主要为路易·德布罗意和埃尔温·薛丁格等等,他们使用的数学工具是微积分,他们共同创建了波动力学。第二个阵营的成员主要为维尔纳·海森堡和马克斯·玻恩等等,使用线性代数,他们建立了矩阵力学。后来,薛丁格证明这两种方法完全等价。[2]:606–609
德布罗意于1924年提出的德布罗意假说表明,每一种微观粒子都具有波粒二象性。电子也不例外,具有这种性质。电子是一种波动,是电子波。电子的能量与动量分别决定了它的物质波频率与波数。既然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应该会有一种能够正确描述这种量子特性的波动方程式,这点子给予埃尔温·薛定谔极大的启示,他因此开始寻找这波动方程式。薛定谔参考威廉·哈密顿先前关于牛顿力学与光学之间的类比这方面的研究,在其中隐藏了一个奥妙的发现,即在零波长极限,物理光学趋向于几何光学;也就是说,光波的轨道趋向于明确的路径,而这路径遵守最小作用量原理。哈密顿认为,在零波长极限,波传播趋向于明确的运动,但他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方程式来描述这波动行为,而薛定谔给出了这方程式。他从哈密顿-雅可比方程成功地推导出薛定谔方程式。[3]:207他又用自己设计的方程式来计算氢原子的谱线,得到的答案与用波耳模型计算出的答案相同。他将这波动方程式与氢原子光谱分析结果,写为一篇论文,1926年,正式发表于物理学界[4][5]:163-167。从此,量子力学有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平台。
薛丁格给出的薛定谔方程式能够正确地描述波函数的量子行为。那时,物理学者尚未能解释波函数的涵义,薛定谔尝试用波函数来代表电荷的密度,但遭到失败。1926年,玻恩提出机率幅的概念,成功地解释了波函数的物理意义[3]:219-220。可是,薛定谔本人不赞同这种统计或机率方法,和它所伴随的非连续性波函数塌缩,如同爱因斯坦认为量子力学只是个决定性理论的统计近似,薛定谔永远无法接受哥本哈根诠释。在他有生最后一年,他写给玻恩的一封信内,薛定谔清楚地表明了这意见。[3]:479
1927年,道格拉斯·哈特里与弗拉基米尔·福克在对于多体波函数的研究踏出了第一步,他们发展出哈特里-福克方程来近似方程的解。这计算方法最先由哈特里提出,后来福克将之加以改善,能够符合包立不相容原理的要求。[6]:344-345
薛定谔方程式不具有劳仑兹不变性 ,无法准确给出符合相对论的结果。薛定谔试著用相对论的能量动量关系式,来寻找一个相对论性方程式,并且描述电子的相对论性量子行为。但是这方程式给出的精细结构不符合阿诺·索末菲的结果,又会给出违背量子力学的负机率和怪异的负能量现象,他只好将这相对论性部分暂时搁置一旁,先行发表前面提到的非相对论性部分。[3]:196-197[7]:3
1926年,奥斯卡·克莱因和沃尔特·戈尔登将电磁相对作用纳入考量,独立地给出薛定谔先前推导出的相对论性部分,并且证明其具有劳仑兹不变性。这方程式后来称为克莱因-戈尔登方程式。[7]:3
1928年,保罗·狄拉克最先成功地统一了狭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他推导出狄拉克方程式,适用于电子等等自旋为1/2的粒子。这方程式的波函数是一个旋量,拥有自旋性质。[5]:167
概述


假设一个自旋为零的粒子移动于一维空间。这粒子的量子态以波函数表示为 ;其中, 是位置, 是时间。波函数是复值函数。测量粒子位置所得到的结果不是决定性的,而是机率性的。粒子的位置 在区间 (即 )的机率为
- ;
其中, 是对于粒子位置做测量的时间。
换句话说, 是粒子在位置 、时间 的机率密度。
这导致归一化条件:在位置空间的任意位置找到粒子的机率为100%:
- 。
在动量空间,粒子的波函数表示为 ;其中, 是一维动量,值域从 至 。测量粒子动量所得到的结果不是决定性的,而是机率性的。粒子的动量 在区间 (即 )的机率为
- 。
动量空间波函数的归一化条件也类似:
- 。

位置空间波函数与动量空间波函数彼此是对方的傅立叶变换。他们各自拥有的信息相同,任何一种波函数都可以用来计算粒子的相关性质。两种波函数之间的关系为[8]:108
- 、
- 。
量子力学中体系的态实际上由一个希尔伯特空间里的 矢量来描述。我们可以用任何不同的基来表示它。[9]
波函数 实际上是 在坐标本征函数为基上展开的“分量”:
(这里基矢量 对应于本征值为 的算符 的本征函数)。[9]
动量空间波函数 是 用动量本征函数的基展开时的展开系数:
(这里基矢量 对应于属于本征值 的 的本征函数)[9][注 3] 。
我们也可以把 用能量本征函数的基展开(简单起见,假设谱是分立的):
(这里基矢量 对应属于 的第 个本征函数:) 。[9]
波函数 与 和系数的集合 ,所有这些所表示的都是同一个状态,包含完全一样的信息——它们仅是描述同一矢量的三种不同途径而已[9]:
薛丁格方程式
在一维空间里,运动于位势 的单独粒子,其波函数满足含时薛丁格方程式
- ;
不含时薛丁格方程式与时间无关,可以用来计算粒子的本征能量与其它相关的量子性质。应用分离变数法,猜想 的函数形式为
- ;
其中, 是分离常数,稍加推导可以论定 就是能量, 是对应于 的本征函数。
代入这猜想解,经过一番运算,可以推导出一维不含时薛丁格方程式:
- 。
波函数的概率诠释
波函数 是概率波。其模的平方 代表粒子在该处出现的概率密度,并且具有归一性,全空间的积分
- 。
波函数的另一个重要特性是相干性。两个波函数叠加,概率的大小取决于两个波函数的相位差,类似光学中的杨氏双缝实验。
波函数的本征值和本征态
在量子力学中,可观察量 以算符 的形式出现。 代表对于波函数的一种运算。例如,在位置空间里,动量算符 的形式为
- 。
可观察量 的本征方程式为
- 。
态叠加原理
假设对于某量子系统测量可观察量 ,而可观察量 的本征态 、 分别拥有本征值 、 ,则根据薛定谔方程的线性关系,叠加态 也可以是这量子系统的量子态:
- ;
其中, 、 分别为叠加态处于本征态 、 的机率幅。
假设对这叠加态系统测量可观察量 ,则测量获得数值是 或 的机率分别为 、 ,期望值为
- 。
定态

在量子力学中,一类基本的问题是哈密顿算符 不含时间的情况。对于这问题,应用分离变数法,可以将波函数 分离成一个只与位置有关的函数 和一个只与时间有关的函数 :
- 。
将这公式代入薛定谔方程,就会得到
- 。
而 则满足本征能量薛丁格方程式:
- 。
例子
3D空间中的自由粒子,其波矢 为k , 角频率 为ω,其波函数为:
粒子被限制在x = 0和x = L之间的1D空间中,其波函数为:[8]:30-38
其中,是能量本征值,是正整数,是质量。

在1D情况下,粒子处于如下势垒中:
其波函数的定态解为(为常数)

量子点是在把激子在三个空间方向上束缚住的半导体纳米结构。粒子在三个方向上都处在势阱中。势阱可以由于静电势(由外部的电极,掺杂,应变,杂质产生),两种不同半导体材料的界面(例如:在自组量子点中),半导体的表面(例如:半导体纳米晶体),或者以上三者的结合。量子点具有分离的量子化的能谱。所对应的波函数在空间上位于量子点中,但延伸于数个晶格周期中。其中的能级可以用类似无限深方形阱的模型来描述,能级位置取决于势阱宽度。
参阅
参考文献
注释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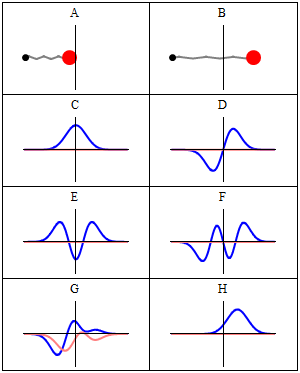









![{\displaystyle [a,b]}](http://wikimedia.org/api/rest_v1/media/math/render/svg/9c4b788fc5c637e26ee98b45f89a5c08c85f79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