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主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在研究設計中,特別是在心理學、社會科學、生命科學和物理學中,「操作主義」是定義對現象的測量的過程,該現象不是直接的可測量的, 現象化是指將無法直接測量的現象轉化為可測量的指標,以便進行研究和分析。例如,健康 這一現象可以通過一個或多個指標來衡量,如 體重指數 或 吸菸。再舉一個例子,在 視覺處理中,可以通過測量某個物體所反射光的特定特徵來推斷它在環境中的存在。在這些例子中,相關現象往往難以直接觀察和測量,因為它們可能是抽象概念(如健康),或者屬於潛在變量。操作主義通過研究這些現象所產生的 可觀察和可測量影響,幫助推斷它們的存在,並明確其某些外延特徵,使其更易於研究和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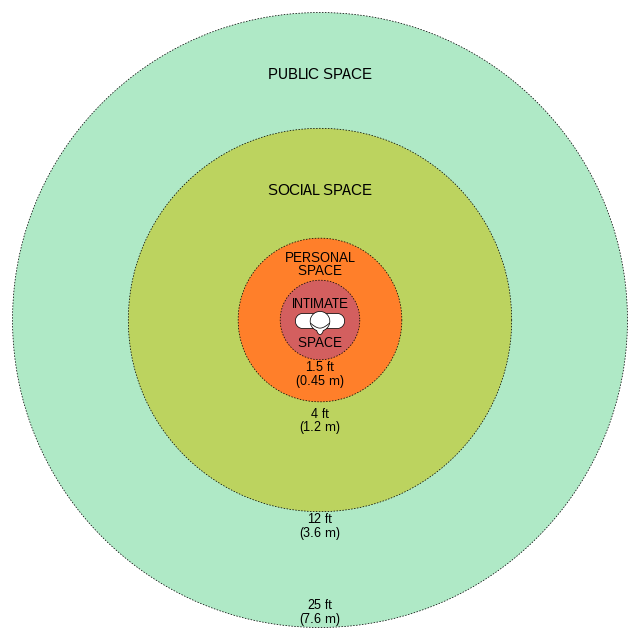
有時候,對於同一現象可能存在多個或相互競爭的操作化方式。通過依次使用不同的操作化方式重複分析,可以判斷結果是否受到不同操作方式的影響。這一過程稱為穩健性檢驗。
操作主義的概念最早由英國物理學家 N. R. Campbell 在他的《物理學:元素》(劍橋,1920 年)中提出。這個概念傳播到 人文科學 和 社會科學。它仍在物理學中使用。 [2][3][4][5][6][7]
操作主義於1920年代產生於美國,由美國實驗物理學家布里奇曼創建,是主張以操作定義科學概念的一種學說,該學說認為:科學概念與相應的操作同義,凡是不能與操作相聯繫,不能由操作定義的概念,都是沒意義的。[8][9]
布里奇曼認為,操作主義的思想方法對整個社會具有廣泛影響:意味著我們整個思想習慣的深刻變化,意味著我們不再容許在思想概念里把我們不能用操作來充分說明的東西當作工具來使用。
布里奇曼的理論受到了批評,因為「長度」可以通過不同的方法測量(例如,無法使用測量尺來測量到月球的距離),因此從邏輯上講,「長度」並不是一個概念,而是多個概念,其中一些概念需要依賴幾何學的知識。[來源請求]。每個概念都需要由所使用的測量操作定義。因此,批評的核心在於,潛在的概念可能是無限的,每個概念都由測量它的方法來定義,例如視角、太陽年的某一天、月球的角直徑等,而這些概念是通過天文學家在數千年間收集的觀測數據整合得出的。
20世紀30年代,哈佛大學的實驗心理學家愛德溫·博林及其學生斯坦利·史密斯·史蒂文斯和道格拉斯·麥格雷戈在面對心理學現象測量的**方法論和認識論問題時,找到了一種解決方案——他們將心理學概念操作化,這一方法最早由他們的哈佛同事布里奇曼在物理學領域提出。這一思路促使史蒂文斯和麥格雷戈從1935年起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在心理學領域引發了廣泛討論,並最終促成了1945年的「操作主義研討會」,布里奇曼也參與了該研討會的討論。[8]
實際的「操作主義」通常被理解為與通過使用 理論 來描述現實的 理論定義 有關。
仔細作化的重要性也許可以在 廣義相對論。愛因斯坦發現科學家們對「質量」有兩種作定義:「慣性」,通過施加力並觀察加速度來定義,來自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和 引力 ,通過將物體放在天平或天平上來定義。以前,沒有人注意所使用的不同作,因為它們總是產生相同的結果,[10]
但愛因斯坦的關鍵洞見在於提出了等效原理,即這兩種操作方式之所以總能得出相同的結果,是因為它們在更深層次上是等價的,並進一步推導出這一假設的含義,從而發展廣義相對論。因此,科學上的這一突破正是通過拋開對科學測量不同操作定義的執著,而認識到它們實際上描述的是同一個理論概念而實現的。然而,愛因斯坦對操作主義方法的否定受到了布里奇曼(P.W. Bridgman)的批評。他在《愛因斯坦的理論與操作主義觀點》一文中指出:「愛因斯坦在廣義相對論中並沒有貫徹他在狹義相對論中教給我們的那些經驗和洞見。」(第335頁)[11]
在社會科學中

操作化通常在社會科學、科學方法和心理測量學中作為一部分使用。特別是在處理複雜概念和複雜刺激的情況下(例如商業研究、軟體工程),往往會出現操作化有效性威脅的特殊關注點。[12]
例如,研究人員可能希望衡量「憤怒」這一概念。憤怒的存在及其情感的深度無法通過外部觀察者直接測量,因為憤怒是無形的。因此,外部觀察者使用其他衡量標準,例如面部表情、詞彙選擇、音量和語氣。
如果研究人員想要衡量不同人群中「憤怒」的深度,最直接的操作方法是問他們一個問題,例如「你生氣嗎?」或「你有多生氣?」然而,這種操作存在問題,因為它依賴於個體的定義。有些人可能會受到輕微的惱怒,變得稍微生氣,但仍然形容自己為「非常生氣」;而其他人可能會受到嚴重的挑釁,變得非常生氣,卻形容自己為「稍微生氣」。此外,在許多情況下,詢問受試者是否生氣也不現實。
由於憤怒的一個衡量標準是音量,研究人員可以通過測量受試者的講話音量與其正常語調的對比,來操作化憤怒這一概念。然而,這必須假設音量是一個統一的衡量標準。有些人可能通過言語作出反應,而其他人則可能通過身體反應來表達憤怒。
社會科學中操作主義的主要批評者之一指出:「最初的目標是消除支配早期心理學理論的主觀**心理主義**概念,並用更具操作性意義的方式來解釋人類行為。但正如經濟學中所見,支持者最終『將操作主義推翻』。」[13]「他們沒有取代『形上學』術語,如『欲望』和『目的』,而是『通過給它們賦予操作性定義來使它們合法化』。」因此,在心理學中,正如在經濟學中一樣,最初相當激進的操作主義思想最終僅僅成為了主流方法論實踐的「安慰符號」。[14][15]
與概念框架的關聯
上述討論將操作化與概念的測量聯繫起來。許多學者致力於對諸如工作滿意度、偏見、憤怒等概念進行操作化。量表和指數的構建是操作化的形式之一。操作化並沒有唯一完美的方式。例如,在美國,「行駛距離」這一概念的操作化單位是英里(miles),而在歐洲則使用公里(kilometers)。[16]
操作化是實證研究過程的一部分。[17]一個例子是實證研究問題:「工作滿意度是否會影響員工離職率」。在研究中,「工作滿意度」和「離職率」這兩個概念都需要被測量。概念本身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都很重要——操作化是在更大的概念框架之中進行的。 當研究問題或研究目的較為宏大時,用於回應問題的概念框架必須在數據收集開始之前被操作化。 如果一位學者基於一個概念框架設計了一份問卷,那就意味著他們已經對該框架進行了操作化。 大多數嚴肅的實證研究都應包含透明的、並與概念框架相關聯的操作化過程。
另一個例子是:假設「工作滿意度會降低員工離職率」,這是一種將兩個概念——「工作滿意度」和「員工離職率」聯繫起來(或構建框架)的方式。 從「工作滿意度」這一想法出發,到設計出一組構成「工作滿意度量表」的問卷題項,這一過程就稱為操作化。 例如,有可能僅用兩個簡單的問題來衡量工作滿意度: 「總的來說,我對自己的工作感到滿意。」 「總體而言,我喜歡我的工作。」[18]
在檢驗正式(定量)假設和工作假設(定性)時,操作化所採用的邏輯是不同的。對於正式假設,概念通過數值變量進行經驗化(或操作化)表示,並通過推論統計進行檢驗。然而,在社會科學和行政科學中常用的工作假設,則是通過證據的收集和評估來進行檢驗的。[19]證據通常是在案例研究的背景下收集的。研究者會問:這些證據是否足以「支持」這一工作假設?正式的操作化過程會具體說明哪些證據能夠支持假設,哪些證據則不能支持。[20]
Robert Yin 建議在進行數據收集階段之前,制定一個案例研究方案,以明確所需證據的類型。他指出,證據有六種來源:文獻資料、檔案記錄、訪談、直接觀察、參與觀察實物或文化遺物[21]在公共管理領域,Patricia M. Shields 和 Tajalli(2006)識別出了五種類型的概念框架:工作假設、描述性類別、實用理想類型、運籌學、正式假設, 他們對每一種概念框架的操作化方式進行了說明與示例說明。他們還展示了如何通過構建與文獻相結合的概念框架表和列出操作化細節的操作化表格,使概念化與操作化更為具體,從而說明如何衡量這些概念。[22][23]
另見
參考文獻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